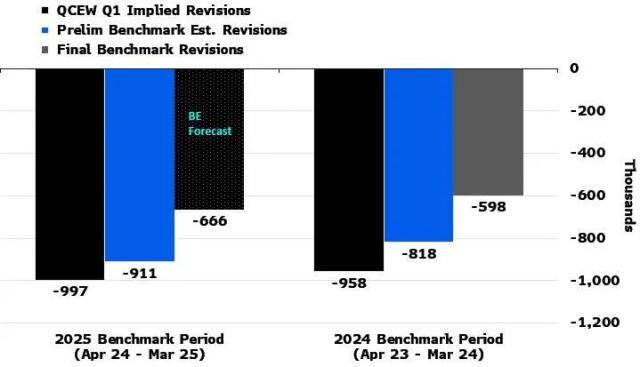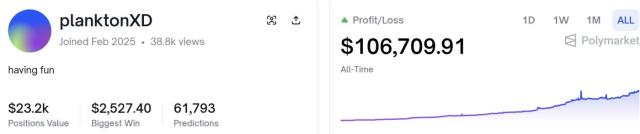当意大利哲学家和散文家安德烈亚·科拉梅迪奇 (Andrea Colamedici) 发布《催眠统治:特朗普、马斯克和现实的新架构》 (Ipnocrazia: Trump, Musk e La Nuova Architettura Della Realtà) 时,他想要对数字时代真理的存在做出陈述。
这本出版于 12 月的书被 Colamedici 联合创办的出版社 Tlon 描述为“一本至关重要的书,它有助于理解当今的控制方式并非压制真相,而是不断增加叙述,让人无法找到任何固定点”。尽管这本书在哲学界引起了热议,但意大利杂志《快报》在 4 月透露,该书所谓的作者荀建伟并不存在,此前该杂志的一位编辑曾试图采访他但未果。荀建伟最初被描述为一位出生于香港、现居柏林的哲学家,后来发现他实际上是人类和算法混合创作的。书中将 Colamedici 列为翻译,他使用人工智能生成概念,然后批判这些概念。
“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哲学实验,一场表演。我的目标是提高人们的意识,”他告诉《连线》杂志。他表示,这本书的初衷是帮助读者理解人工智能,并为这个时代创造一个全新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 《催眠统治:特朗普、马斯克和现实的新架构》已有三种语言版本(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销量约为 5,000 册。
本书简介写道:“从特朗普、马斯克等世界领袖人物,到数字平台如何吸引我们的注意力,Xun揭示了权力塑造我们对现实感知的机制。这是一次清晰而令人不安的分析,它超越了对数字社会的传统批判,揭示了现实本身如何沦为政治战场。”
然而,围绕使用人工智能来创作它并最初保留这些信息的决定的争议现在已经成为围绕它的讨论的主要部分 - 而这正是 Colamedici 想要的。
“当读者发现这本书创作的真相时,很多人都受到了伤害。我对此深感遗憾,但这是必要的。”他说。
《连线》杂志采访了科拉梅迪奇,探讨了他的项目的细节。
本次采访已进行编辑,以便简洁和清晰。
《连线》:这个哲学实验的灵感是什么?
Andrea Colamedici:首先,我在欧洲设计学院教授即时思维,并在福贾大学领导一个关于人工智能和思维系统的研究项目。在与学生们的合作中,我意识到他们使用ChatGPT的方式极其糟糕:抄袭。我发现,他们对人工智能的依赖正在让他们对生活失去理解。这令人担忧,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海量知识的时代,却不知该如何运用。我经常告诫他们:“你可以用ChatGPT作弊获得好成绩,甚至成就一番事业,但最终你会变得一无所有。” 我培训过几所意大利大学的教授,许多人问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学习ChatGPT?” 答案是永远停止。重要的不是完成人工智能教育,而是如何在使用过程中学习。
我们必须保持好奇心,同时正确使用这一工具,并教会它如何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运作。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关键的区别:有些信息会让你变得被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侵蚀你的思考能力;而有些信息则会挑战你,让你变得更聪明,超越你的极限。我们应该这样使用人工智能:将其作为帮助我们以不同方式思考的对话者。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这些工具是由大型科技公司设计的,这些公司强加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他们选择数据,选择数据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是,他们把我们视为需要我们满意的客户。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使用人工智能,它只会强化我们的偏见。我们会认为自己是对的,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思考;我们将被数字化所包围。我们承受不起这种麻木。这正是本书的出发点。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描述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吉尔·德勒兹来说,哲学是创造概念的能力,而今天我们需要新的概念来理解我们的现实。没有这些概念,我们将迷失方向。看看特朗普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加沙视频,或者像马斯克这样的人物的挑衅就知道了。没有坚实的概念工具,我们就会陷入困境。优秀的哲学家会创造像钥匙一样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世界。
您写这本新书的目的是什么?
这本书力求做到三件事:帮助读者了解人工智能;为这个时代发明一个新概念;以及兼顾理论和实践。当读者发现这本书创作的真相时,许多人都受到了伤害。我对此深感遗憾,但这是必要的。有人说:“我希望有这样的作者存在。” 好吧,他确实不存在。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构建着自己的叙事。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极右翼就会垄断叙事,制造神话,而我们将在他们书写历史的同时,耗费一生去核实事实。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您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帮助您撰写这篇哲学论文的?
我想澄清一下,这篇文章并非由人工智能撰写。是的,我的确使用了人工智能,但并非以传统的方式。我开发了一种基于创造对立面的方法,并在欧洲设计学院教授。这是一种以对抗性的方式思考和运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我没有要求机器替我写作,而是让它产生想法,然后我使用GPT和Claude对其进行批判,让我对自己所写的内容提出新的视角。书中所写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人工智能是我们必须学会使用的工具,因为如果我们滥用它——“滥用”包括把它当作某种神谕,要求它“告诉我世界问题的答案;解释我为什么存在”——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思考的能力。我们会变得愚蠢。20世纪90年代的伟大艺术家白南准曾说过:“我利用科技是为了真正地憎恨它。”而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理解它,因为如果我们不理解,它就会利用我们。人工智能将成为大型科技公司控制和操纵我们的工具。我们必须学会正确使用这些工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您选择以翻译家而不是作家的身份来展现自己?
我用“翻译”来比喻。是的,我就是翻译,但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翻译。我之所以是翻译,是因为翻译也可以理解为运输,而这正是我的工作:我运输某种东西。然而,这本书是用意大利语写的。我既不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我不懂中文——也不是从英文(小说人物荀建伟懂的另一种语言)翻译过来的。荀建伟是一个边缘人物:东西方的交汇点,文化碰撞的点。而这正是他提供的机会,让我们理解我们必须在人工智能这些陌生的空间里相遇。我们可以做到,但我们必须谨慎而勇敢地前行。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矛盾,但这就是我们必须体现这种联系的方式。在这里成为一名翻译,也是在翻译一个历史性机遇:反思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反思这一点,我们将仅仅是被动的主体。这必须被问题化。我们不能只是说“人工智能,给我更多,更多,更多。”我们既不能成为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切的科技狂热分子,也不能成为科技恐惧者,因为如今没有科技就无法生存。人工智能已然存在,我们必须理解它。它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生活的机会,我们必须抓住它。
如果人工智能都能创作出令人信服的哲学论文,那么人类作家还能做什么呢?您曾说过“我们必须思考,我们必须批判”。那么,当今知识分子的前进方向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美的问题,因为如果人工智能比我们画得更好,如果它开车比我们开得更好,如果它能比我们更好地创作音乐……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但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用新自由主义的视角,把所有生命都变成了一场以胜负为目的的竞争。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必须追求自身的个人成就,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无论有没有人工智能。别人画得比我好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学习画得更好,提升自己的能力——与人工智能合作,或者与其他人合作(我建议与人合作,但如果你选择人工智能,那也没关系)。人类最大的问题在于痴迷于成为第一,成为故事的中心。但科学在19世纪就已经向我们表明,我们并非宇宙的中心;我们位于银河系的一个遥远角落。我们甚至也不是地球生命的中心:超过99%的生物量是植物、树木和其他生命形式。我们如此渺小,我们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仅仅20万年。想想松树或其他物种;鸡,它是一个更古老的物种。即使在人类中,我们也不是一个整体。正如沃尔特·惠特曼所说:“我庞大,我包含众多。” 我们也不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这不必被理解为一种悲剧,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解放。
我们来聊聊《催眠统治》( Ipnocrazia )。你为什么给你的书取这个名字?顺便再深入聊聊你在书中分析的特朗普和马斯克的关系。
是的,我之所以说催眠,是因为正在发生的并非某种力量对我们身体或思想的物理作用,而是对我们意识状态本身的操控。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他们通过算法操纵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这真的很危险。当我们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时,我们以为自己与世界相连。我们阅读报纸,但我们收到的却是一条个性化的时间线,为我们量身定制了一个现实。
这非常令人担忧。我们自以为与他人共处一室,但现实却被我们的偏见、观点和政治立场所塑造。我们需要与那些想法不同的人接触,但这些过滤气泡和回音室只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必须架起通往未知、通往差异的桥梁。否则,我们将走向内战。他人将成为威胁,而事实上,他们首先是一个谜,甚至可能是值得珍惜的东西。这应该是我们面对差异时首先想到的。
人工智能能拥有原创的观点吗?或者催眠统治只是通过算法重复利用人类的思维?您如何定义这种关系?
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其中存在一个悖论:催眠术始于人类视角。没有它,它就不会存在。但与此同时,如果没有人工智能,我也无法构思出这个概念。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相互依赖:正如我需要与他人对话来发展一个想法一样,我也需要与人工智能进行对话。人工智能并非独立存在。它需要提示和刺激,而人类则可以自主思考。但这正是我们必须理解人工智能的原因。如果我们不尊重它作为工具的本质,最终会贬低我们自身的人性。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习惯用一种非人性的语气说“Alexa,关灯”,我们最终也会用同样的方式与伴侣或朋友交谈。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像感谢Siri那样感谢她,因为她没有感情,而是说我们应该确保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表达善意的能力。
一些耐人寻味的研究表明,当我们通过应用程序叫车时,对待司机的态度比打电话叫车更糟糕。这种做法的风险是双重的:将人工智能人性化(它当然不是人类)和将人“平台化”(即将人变成界面)。这很危险,混淆这些不同类型的交流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人性。
您认为人工智能仅仅是人类的工具吗,或者您如何定义它的本体论地位?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工具。它是我们过去的产物,是我们创造的一种集体意识,它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为何存在。但这里有一个悖论: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告诉我们天气预报、背诵古代诗人的诗句,或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但它永远无法帮助我们理解生命的意义。
错误在于问人工智能“我为什么存在”。更好的方法是告诉它:“我一直在思考生命的意义。我读过萨特的著作,他说意义并非预先确定,而是我们构建的。为了拓宽我的理解,你建议我阅读哪些其他文化的思想家的作品?”西方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需要找到其他根本性的联系:与美洲原住民哲学、吠陀经和其他遥远文化的联系。人工智能的巨大机遇就在于此:它不是神谕,而是通往未知的桥梁。
是什么促使你选择荀建伟这个国籍,以及这位虚构哲学家所处的文化背景?是你自己的决定,还是人工智能的产物,又或者是为了挑战某些西方叙事的策略?
世界需要明白,西方文化必须放眼自身之外。西方文明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仍然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而其他文化充其量只能是复制品。这是一个深刻的错误。今天,真正具有革命性的东西——那些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思想——不会来自西方。它们可能来自中国,但更有可能来自当今不同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我们需要警惕,即使是“东方”和“西方”的概念也是一种荒谬的简化,但我暂时使用它们。
我想创造一种超越西方自恋的视角。一种将新事物与古老却被遗忘的思维方式相结合的视角。例如,在意大利,我们面临着一种疯狂的局面:政府要求学校教授只有我们才有历史。你能想象吗?仿佛中国的历代王朝,或是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都没有历史似的。这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脆弱性,它不去承认自己正在失去中心地位——这并非悲剧,而是一种解放——而是执着于荒谬的神话。
这本书已经成为一种出版现象。您认为它的成功源于什么?是人们对人工智能话题的兴趣、哲学上的挑战,还是数字时代关于作者身份的争论?
确实我们已经加印了三次,虽然我不记得每次加印了2000册还是3000册。这本书总共卖出了4000到5000册。但最奇怪的是,一位来自西班牙报纸《国家报》( El País)的记者联系我,问我:“你用笔名是为了卖更多册吗?” 事实恰恰相反!在意大利,我的书已经卖得很好了;我不需要再起其他名字。实际上,第一次加印只有70册;那是一个实验。后来我发现这个概念引起了读者的共鸣,我们就增加了印刷量。
现在我的生活一团糟。我要去五个国家采访,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活动日程也排得满满的。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虽然很有趣,但也很重要。玩乐并非无足轻重:如果我们不玩乐,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们正处于一个黑暗的历史时刻;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我们的生存方式。
当《国家报》得知这本书的哲学家兼合著者并非真实存在时,他们决定从网站上删除该书的评论。如果这本书的论点站得住脚,并且它引发了一场重要的辩论,为什么不去探究其背景,而是直接删除它呢?您认为这是否反映了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无法处理虚构与真相之间的模糊性?
我理解这种担忧。新闻业正遭受攻击,许多媒体机构出于担心信誉受损而采取行动。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攻击他们认为的“冒名顶替者”,并抹去所有痕迹。这种反应可以理解,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保护记者。记者对于揭露真相和重建专家的信任至关重要。但《国家报》的错误在于没有花时间去了解背景。例如,他们谈论的是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但在2023年,我参加了欧盟峰会(SOTEU),并聆听了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讲话。她承认,技术发展速度快于监管,立法很复杂,因为创新迫在眉睫。 《国家报》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与其删除这篇评论,不如写一些更细致入微的内容,例如“是的,作者是虚构的,但他对人工智能的分析很有意义,因为……”
然而,我理解媒体为何如此行事:他们选择谨慎行事。问题在于,这并非最明智的解决方案。明智的做法是开启对话,接受没有人完全了解人工智能的现实。这是一个庞大且不断变化的领域,我们应该鼓励好奇心作为驱动力。人们感到疲惫和恐惧,但好奇心能够激发能量。我们需要更复杂的讨论,而不是受恐惧驱使的简单化。
这本书背后的游戏,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揭示了一个悖论:读者明知这位虚构的哲学家并非真实存在,却依然对他产生共鸣。这难道不正表明,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更渴望可信的故事,而非真实的事实吗?
我不知道。现在读者知道这本书比最初看起来要复杂得多,我们拭目以待。以前,读者被书中引人入胜的理论所吸引;现在他们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要理解文本的真正结构——或许要读到最后才能理解;二是要明白“作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我读过一些意大利媒体的文章,它们体现了一种荒谬的矛盾。他们深入研究,但标题却把这本书简化成最耸人听闻的部分:“人工智能创造的哲学家”。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本书并非人工智能写的,而是对作者身份和真理概念的探究。我知道很难用一个标题来概括,但我们应该花几分钟时间思考一下。否则,我们就会助长一种简化思想、散播不信任的倾向。我们对读者负有重大责任。
一个更微妙的标题可能是“人工智能哲学家还是我们时代的缩影?”但我们更喜欢轻松点击。如今,我们的世界只围绕着眼前的回报运转,即便我们应该鼓励更缓慢的追求——冥想和富有成效的无聊。正如沃尔特·本雅明所说:“无聊是孵出经验之蛋的梦鸟。”你必须坐在蛋上,等待它孵化。
您是否认为未来还会有其他与人工智能类似的合作?或者这只是一次性的事情,是对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一名作家的意义的一种质疑?
我会继续以荀建伟的名义发表作品——他是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桥梁——但这不会是我唯一的声音。开始认为我只能通过算法表达自己是危险的。我需要在有人工智能的情况下写作,也可以在没有人工智能的情况下写作,因为我必须保持不借助中介而深入自我的能力。目前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但一两年后,我们就会明白这一时刻的风险。我们正濒临失去不依赖科技思考和生活的能力。矛盾的是,人工智能本身,如果使用得当,可以成为一剂解药。它就像一团火,当它以可控的方式燃烧时,会温暖我们,而不会伤害我们。
当读者发现这位“哲学家”实际上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思维的融合时,许多人表示困惑甚至失望。您会如何评价这部融合作品的价值?了解了这本书的真正结构后,他们该如何阅读?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它与百分比无关——比如,Jianwei Xun 并不是 30% 的人工智能和 70% 的人类。Jianwei Xun 是我在研究人工智能时使用的名字。它是一种人类与算法融合的身份,没有任何明确的界限。我想告诉读者,享受这段旅程,让自己感到惊奇,因为惊奇的感觉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正如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所说,哲学源于thaumazein ,这是一个希腊词,既有惊奇或惊讶的意思,也有恐惧的意思。这正是我们的历史时刻:它有两种不同的可怕含义——可怕和令人敬畏。这不是盲目Optimism的问题,即使下雨也坚持认为天气晴朗,而是选择如何看待的问题。这是选择看向深渊之外,知道我们可能会迷失,但我们并不孤单。
真正的自由——以及我们抵御操纵的防御之道——在于主动选择拥抱神秘与未知,即使它令人恐惧。只有这样,科技才能成为桥梁,而非牢笼。
您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哲学未来是什么?为什么您认为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反思这些问题?
哲学的未来存在于我们所谓的“常态”之间的裂缝中。交叉女权主义教导我们,所有真理都有层次——不仅在围绕性别的斗争中,也存在于现实的方方面面。然而,我们却依然假装存在纯粹的身体、思想和观念。
最后一点: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用自己的尺度衡量智力,却忽略了森林拥有记忆,章鱼也会做梦的事实。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我们的冰箱和家门锁中,如同现代的骗子神明一般。这仿佛是托特神话的复活:柏拉图警告说,书写,这种“记忆的毒药”,只会让我们成为纸面上的圣贤。如今,人工智能重演了这一悖论:它承诺知识,却又掏空了认知行为的意义。诀窍在于效仿柏拉图,将这种毒药作为解药。用机器批判机器,用写作来写作,用思考来对抗思想。最终,未来的哲学将不再是避难所,而是一种激励。它将用比任何算法都更尖锐的问题,将我们从技术官僚的梦境中唤醒。
本次采访最初发表于《连线》西班牙语版。由约翰·牛顿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