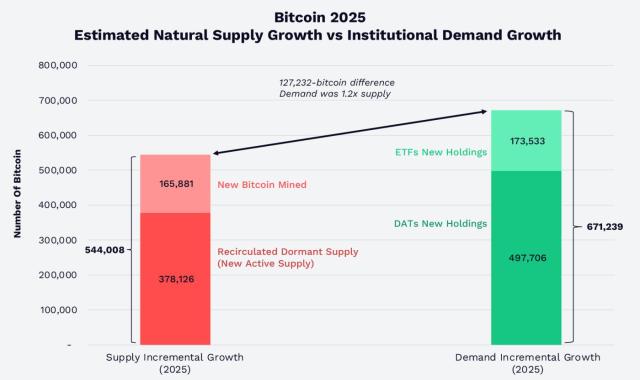當意大利哲學家和散文家安德烈亞·科拉梅迪奇 (Andrea Colamedici) 發佈《催眠統治:特朗普、馬斯克和現實的新架構》 (Ipnocrazia: Trump, Musk e La Nuova Architettura Della Realtà) 時,他想要對數字時代真理的存在做出陳述。
這本出版於 12 月的書被 Colamedici 聯合創辦的出版社 Tlon 描述為“一本至關重要的書,它有助於理解當今的控制方式並非壓制真相,而是不斷增加敘述,讓人無法找到任何固定點”。儘管這本書在哲學界引起了熱議,但意大利雜誌《快報》在 4 月透露,該書所謂的作者荀建偉並不存在,此前該雜誌的一位編輯曾試圖採訪他但未果。荀建偉最初被描述為一位出生於香港、現居柏林的哲學家,後來發現他實際上是人類和算法混合創作的。書中將 Colamedici 列為翻譯,他使用人工智能生成概念,然後批判這些概念。
“這不僅僅是一本書,更是一次哲學實驗,一場表演。我的目標是提高人們的意識,”他告訴《連線》雜誌。他表示,這本書的初衷是幫助讀者理解人工智能,併為這個時代創造一個全新的概念。
到目前為止, 《催眠統治:特朗普、馬斯克和現實的新架構》已有三種語言版本(西班牙語、法語和意大利語),銷量約為 5,000 冊。
本書簡介寫道:“從特朗普、馬斯克等世界領袖人物,到數字平臺如何吸引我們的注意力,Xun揭示了權力塑造我們對現實感知的機制。這是一次清晰而令人不安的分析,它超越了對數字社會的傳統批判,揭示了現實本身如何淪為政治戰場。”
然而,圍繞使用人工智能來創作它並最初保留這些信息的決定的爭議現在已經成為圍繞它的討論的主要部分 - 而這正是 Colamedici 想要的。
“當讀者發現這本書創作的真相時,很多人都受到了傷害。我對此深感遺憾,但這是必要的。”他說。
《連線》雜誌採訪了科拉梅迪奇,探討了他的項目的細節。
本次採訪已進行編輯,以便簡潔和清晰。
《連線》:這個哲學實驗的靈感是什麼?
Andrea Colamedici:首先,我在歐洲設計學院教授即時思維,並在福賈大學領導一個關於人工智能和思維繫統的研究項目。在與學生們的合作中,我意識到他們使用ChatGPT的方式極其糟糕:抄襲。我發現,他們對人工智能的依賴正在讓他們對生活失去理解。這令人擔憂,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擁有海量知識的時代,卻不知該如何運用。我經常告誡他們:“你可以用ChatGPT作弊獲得好成績,甚至成就一番事業,但最終你會變得一無所有。” 我培訓過幾所意大利大學的教授,許多人問我:“我什麼時候才能停止學習ChatGPT?” 答案是永遠停止。重要的不是完成人工智能教育,而是如何在使用過程中學習。
我們必須保持好奇心,同時正確使用這一工具,並教會它如何按照我們想要的方式運作。這一切都源於一個關鍵的區別:有些信息會讓你變得被動,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會侵蝕你的思考能力;而有些信息則會挑戰你,讓你變得更聰明,超越你的極限。我們應該這樣使用人工智能:將其作為幫助我們以不同方式思考的對話者。否則,我們將無法理解這些工具是由大型科技公司設計的,這些公司強加了特定的意識形態。他們選擇數據,選擇數據之間的聯繫,最重要的是,他們把我們視為需要我們滿意的客戶。如果我們以這種方式使用人工智能,它只會強化我們的偏見。我們會認為自己是對的,但實際上我們並沒有思考;我們將被數字化所包圍。我們承受不起這種麻木。這正是本書的出發點。第二個挑戰是如何描述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對吉爾·德勒茲來說,哲學是創造概念的能力,而今天我們需要新的概念來理解我們的現實。沒有這些概念,我們將迷失方向。看看特朗普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加沙視頻,或者像馬斯克這樣的人物的挑釁就知道了。沒有堅實的概念工具,我們就會陷入困境。優秀的哲學家會創造像鑰匙一樣的概念,幫助我們理解世界。
您寫這本新書的目的是什麼?
這本書力求做到三件事:幫助讀者瞭解人工智能;為這個時代發明一個新概念;以及兼顧理論和實踐。當讀者發現這本書創作的真相時,許多人都受到了傷害。我對此深感遺憾,但這是必要的。有人說:“我希望有這樣的作者存在。” 好吧,他確實不存在。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構建著自己的敘事。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極右翼就會壟斷敘事,製造神話,而我們將在他們書寫歷史的同時,耗費一生去核實事實。我們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您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來幫助您撰寫這篇哲學論文的?
我想澄清一下,這篇文章並非由人工智能撰寫。是的,我的確使用了人工智能,但並非以傳統的方式。我開發了一種基於創造對立面的方法,並在歐洲設計學院教授。這是一種以對抗性的方式思考和運用機器學習的方法。我沒有要求機器替我寫作,而是讓它產生想法,然後我使用GPT和Claude對其進行批判,讓我對自己所寫的內容提出新的視角。書中所寫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人工智能是我們必須學會使用的工具,因為如果我們濫用它——“濫用”包括把它當作某種神諭,要求它“告訴我世界問題的答案;解釋我為什麼存在”——那麼我們就會失去思考的能力。我們會變得愚蠢。20世紀90年代的偉大藝術家白南準曾說過:“我利用科技是為了真正地憎恨它。”而這正是我們必須做的:理解它,因為如果我們不理解,它就會利用我們。人工智能將成為大型科技公司控制和操縱我們的工具。我們必須學會正確使用這些工具,否則,我們將面臨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您選擇以翻譯家而不是作家的身份來展現自己?
我用“翻譯”來比喻。是的,我就是翻譯,但並非字面意義上的翻譯。我之所以是翻譯,是因為翻譯也可以理解為運輸,而這正是我的工作:我運輸某種東西。然而,這本書是用意大利語寫的。我既不是從中文翻譯過來的——我不懂中文——也不是從英文(小說人物荀建偉懂的另一種語言)翻譯過來的。荀建偉是一個邊緣人物:東西方的交匯點,文化碰撞的點。而這正是他提供的機會,讓我們理解我們必須在人工智能這些陌生的空間裡相遇。我們可以做到,但我們必須謹慎而勇敢地前行。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矛盾,但這就是我們必須體現這種聯繫的方式。在這裡成為一名翻譯,也是在翻譯一個歷史性機遇:反思我們所做的事情。如果我們不反思這一點,我們將僅僅是被動的主體。這必須被問題化。我們不能只是說“人工智能,給我更多,更多,更多。”我們既不能成為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切的科技狂熱分子,也不能成為科技恐懼者,因為如今沒有科技就無法生存。人工智能已然存在,我們必須理解它。它為我們提供了更深入生活的機會,我們必須抓住它。
如果人工智能都能創作出令人信服的哲學論文,那麼人類作家還能做什麼呢?您曾說過“我們必須思考,我們必須批判”。那麼,當今知識分子的前進方向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美的問題,因為如果人工智能比我們畫得更好,如果它開車比我們開得更好,如果它能比我們更好地創作音樂……那我們在這裡做什麼呢?但我們應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而不是用新自由主義的視角,把所有生命都變成了一場以勝負為目的的競爭。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必須追求自身的個人成就,找到一種表達自我的方式,無論有沒有人工智能。別人畫得比我好又有什麼關係呢?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學習畫得更好,提升自己的能力——與人工智能合作,或者與其他人合作(我建議與人合作,但如果你選擇人工智能,那也沒關係)。人類最大的問題在於痴迷於成為第一,成為故事的中心。但科學在19世紀就已經向我們表明,我們並非宇宙的中心;我們位於銀河系的一個遙遠角落。我們甚至也不是地球生命的中心:超過99%的生物量是植物、樹木和其他生命形式。我們如此渺小,我們存在的時間非常短暫,僅僅20萬年。想想松樹或其他物種;雞,它是一個更古老的物種。即使在人類中,我們也不是一個整體。正如沃爾特·惠特曼所說:“我龐大,我包含眾多。” 我們也不是地球上最聰明的物種。這不必被理解為一種悲劇,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解放。
我們來聊聊《催眠統治》( Ipnocrazia )。你為什麼給你的書取這個名字?順便再深入聊聊你在書中分析的特朗普和馬斯克的關係。
是的,我之所以說催眠,是因為正在發生的並非某種力量對我們身體或思想的物理作用,而是對我們意識狀態本身的操控。這就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他們通過算法操縱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這真的很危險。當我們使用智能手機和社交網絡時,我們以為自己與世界相連。我們閱讀報紙,但我們收到的卻是一條個性化的時間線,為我們量身定製了一個現實。
這非常令人擔憂。我們自以為與他人共處一室,但現實卻被我們的偏見、觀點和政治立場所塑造。我們需要與那些想法不同的人接觸,但這些過濾氣泡和迴音室只會讓我們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們必須架起通往未知、通往差異的橋樑。否則,我們將走向內戰。他人將成為威脅,而事實上,他們首先是一個謎,甚至可能是值得珍惜的東西。這應該是我們面對差異時首先想到的。
人工智能能擁有原創的觀點嗎?或者催眠統治只是通過算法重複利用人類的思維?您如何定義這種關係?
這又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其中存在一個悖論:催眠術始於人類視角。沒有它,它就不會存在。但與此同時,如果沒有人工智能,我也無法構思出這個概念。這是一種創造性的相互依賴:正如我需要與他人對話來發展一個想法一樣,我也需要與人工智能進行對話。人工智能並非獨立存在。它需要提示和刺激,而人類則可以自主思考。但這正是我們必須理解人工智能的原因。如果我們不尊重它作為工具的本質,最終會貶低我們自身的人性。舉個例子:如果我們習慣用一種非人性的語氣說“Alexa,關燈”,我們最終也會用同樣的方式與伴侶或朋友交談。我並不是說我們需要像感謝Siri那樣感謝她,因為她沒有感情,而是說我們應該確保在現實生活中保持表達善意的能力。
一些耐人尋味的研究表明,當我們通過應用程序叫車時,對待司機的態度比打電話叫車更糟糕。這種做法的風險是雙重的:將人工智能人性化(它當然不是人類)和將人“平臺化”(即將人變成界面)。這很危險,混淆這些不同類型的交流可能會讓我們失去人性。
您認為人工智能僅僅是人類的工具嗎,或者您如何定義它的本體論地位?
毫無疑問,人工智能是人類的工具。它是我們過去的產物,是我們創造的一種集體意識,它幫助我們理解我們為何存在。但這裡有一個悖論:雖然人工智能可以告訴我們天氣預報、背誦古代詩人的詩句,或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案,但它永遠無法幫助我們理解生命的意義。
錯誤在於問人工智能“我為什麼存在”。更好的方法是告訴它:“我一直在思考生命的意義。我讀過薩特的著作,他說意義並非預先確定,而是我們構建的。為了拓寬我的理解,你建議我閱讀哪些其他文化的思想家的作品?”西方已經筋疲力盡了。我們需要找到其他根本性的聯繫:與美洲原住民哲學、吠陀經和其他遙遠文化的聯繫。人工智能的巨大機遇就在於此:它不是神諭,而是通往未知的橋樑。
是什麼促使你選擇荀建偉這個國籍,以及這位虛構哲學家所處的文化背景?是你自己的決定,還是人工智能的產物,又或者是為了挑戰某些西方敘事的策略?
世界需要明白,西方文化必須放眼自身之外。西方文明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它仍然認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是唯一能夠解決問題的,而其他文化充其量只能是複製品。這是一個深刻的錯誤。今天,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東西——那些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世界觀的思想——不會來自西方。它們可能來自中國,但更有可能來自當今不同文化交匯的前沿地帶。我們需要警惕,即使是“東方”和“西方”的概念也是一種荒謬的簡化,但我暫時使用它們。
我想創造一種超越西方自戀的視角。一種將新事物與古老卻被遺忘的思維方式相結合的視角。例如,在意大利,我們面臨著一種瘋狂的局面:政府要求學校教授只有我們才有歷史。你能想象嗎?彷彿中國的歷代王朝,或是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都沒有歷史似的。這反映了一個社會的脆弱性,它不去承認自己正在失去中心地位——這並非悲劇,而是一種解放——而是執著於荒謬的神話。
這本書已經成為一種出版現象。您認為它的成功源於什麼?是人們對人工智能話題的興趣、哲學上的挑戰,還是數字時代關於作者身份的爭論?
確實我們已經加印了三次,雖然我不記得每次加印了2000冊還是3000冊。這本書總共賣出了4000到5000冊。但最奇怪的是,一位來自西班牙報紙《國家報》( El País)的記者聯繫我,問我:“你用筆名是為了賣更多冊嗎?” 事實恰恰相反!在意大利,我的書已經賣得很好了;我不需要再起其他名字。實際上,第一次加印只有70冊;那是一個實驗。後來我發現這個概念引起了讀者的共鳴,我們就增加了印刷量。
現在我的生活一團糟。我要去五個國家採訪,在法國和西班牙的活動日程也排得滿滿的。但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雖然很有趣,但也很重要。玩樂並非無足輕重:如果我們不玩樂,那我們活著還有什麼意義?我們正處於一個黑暗的歷史時刻;我們需要重新定義我們的生存方式。
當《國家報》得知這本書的哲學家兼合著者並非真實存在時,他們決定從網站上刪除該書的評論。如果這本書的論點站得住腳,並且它引發了一場重要的辯論,為什麼不去探究其背景,而是直接刪除它呢?您認為這是否反映了我們在人工智能時代無法處理虛構與真相之間的模糊性?
我理解這種擔憂。新聞業正遭受攻擊,許多媒體機構出於擔心信譽受損而採取行動。他們的第一反應是攻擊他們認為的“冒名頂替者”,並抹去所有痕跡。這種反應可以理解,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必須保護記者。記者對於揭露真相和重建專家的信任至關重要。但《國家報》的錯誤在於沒有花時間去了解背景。例如,他們談論的是歐盟的《人工智能法案》,但在2023年,我參加了歐盟峰會(SOTEU),並聆聽了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的講話。她承認,技術發展速度快於監管,立法很複雜,因為創新迫在眉睫。 《國家報》本可以更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與其刪除這篇評論,不如寫一些更細緻入微的內容,例如“是的,作者是虛構的,但他對人工智能的分析很有意義,因為……”
然而,我理解媒體為何如此行事:他們選擇謹慎行事。問題在於,這並非最明智的解決方案。明智的做法是開啟對話,接受沒有人完全瞭解人工智能的現實。這是一個龐大且不斷變化的領域,我們應該鼓勵好奇心作為驅動力。人們感到疲憊和恐懼,但好奇心能夠激發能量。我們需要更復雜的討論,而不是受恐懼驅使的簡單化。
這本書背後的遊戲,如果你願意這麼說的話,揭示了一個悖論:讀者明知這位虛構的哲學家並非真實存在,卻依然對他產生共鳴。這難道不正表明,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更渴望可信的故事,而非真實的事實嗎?
我不知道。現在讀者知道這本書比最初看起來要複雜得多,我們拭目以待。以前,讀者被書中引人入勝的理論所吸引;現在他們面臨兩大挑戰:一是要理解文本的真正結構——或許要讀到最後才能理解;二是要明白“作者”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作者。我讀過一些意大利媒體的文章,它們體現了一種荒謬的矛盾。他們深入研究,但標題卻把這本書簡化成最聳人聽聞的部分:“人工智能創造的哲學家”。但事實並非如此,這本書並非人工智能寫的,而是對作者身份和真理概念的探究。我知道很難用一個標題來概括,但我們應該花幾分鐘時間思考一下。否則,我們就會助長一種簡化思想、散播不信任的傾向。我們對讀者負有重大責任。
一個更微妙的標題可能是“人工智能哲學家還是我們時代的縮影?”但我們更喜歡輕鬆點擊。如今,我們的世界只圍繞著眼前的回報運轉,即便我們應該鼓勵更緩慢的追求——冥想和富有成效的無聊。正如沃爾特·本雅明所說:“無聊是孵出經驗之蛋的夢鳥。”你必須坐在蛋上,等待它孵化。
您是否認為未來還會有其他與人工智能類似的合作?或者這只是一次性的事情,是對在我們這個時代成為一名作家的意義的一種質疑?
我會繼續以荀建偉的名義發表作品——他是人類與人工智能之間的橋樑——但這不會是我唯一的聲音。開始認為我只能通過算法表達自己是危險的。我需要在有人工智能的情況下寫作,也可以在沒有人工智能的情況下寫作,因為我必須保持不借助中介而深入自我的能力。目前並非所有人都意識到這一點,但一兩年後,我們就會明白這一時刻的風險。我們正瀕臨失去不依賴科技思考和生活的能力。矛盾的是,人工智能本身,如果使用得當,可以成為一劑解藥。它就像一團火,當它以可控的方式燃燒時,會溫暖我們,而不會傷害我們。
當讀者發現這位“哲學家”實際上是人工智能與人類思維的融合時,許多人表示困惑甚至失望。您會如何評價這部融合作品的價值?瞭解了這本書的真正結構後,他們該如何閱讀?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因為它與百分比無關——比如,Jianwei Xun 並不是 30% 的人工智能和 70% 的人類。Jianwei Xun 是我在研究人工智能時使用的名字。它是一種人類與算法融合的身份,沒有任何明確的界限。我想告訴讀者,享受這段旅程,讓自己感到驚奇,因為驚奇的感覺是我們今天所缺乏的。正如柏拉圖在《泰阿泰德篇》中所說,哲學源於thaumazein ,這是一個希臘詞,既有驚奇或驚訝的意思,也有恐懼的意思。這正是我們的歷史時刻:它有兩種不同的可怕含義——可怕和令人敬畏。這不是盲目Optimism的問題,即使下雨也堅持認為天氣晴朗,而是選擇如何看待的問題。這是選擇看向深淵之外,知道我們可能會迷失,但我們並不孤單。
真正的自由——以及我們抵禦操縱的防禦之道——在於主動選擇擁抱神秘與未知,即使它令人恐懼。只有這樣,科技才能成為橋樑,而非牢籠。
您認為人工智能時代的哲學未來是什麼?為什麼您認為我們現在迫切需要反思這些問題?
哲學的未來存在於我們所謂的“常態”之間的裂縫中。交叉女權主義教導我們,所有真理都有層次——不僅在圍繞性別的鬥爭中,也存在於現實的方方面面。然而,我們卻依然假裝存在純粹的身體、思想和觀念。
最後一點: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用自己的尺度衡量智力,卻忽略了森林擁有記憶,章魚也會做夢的事實。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正悄無聲息地滲透到我們的冰箱和家門鎖中,如同現代的騙子神明一般。這彷彿是托特神話的復活:柏拉圖警告說,書寫,這種“記憶的毒藥”,只會讓我們成為紙面上的聖賢。如今,人工智能重演了這一悖論:它承諾知識,卻又掏空了認知行為的意義。訣竅在於效仿柏拉圖,將這種毒藥作為解藥。用機器批判機器,用寫作來寫作,用思考來對抗思想。最終,未來的哲學將不再是避難所,而是一種激勵。它將用比任何算法都更尖銳的問題,將我們從技術官僚的夢境中喚醒。
本次採訪最初發表於《連線》西班牙語版。由約翰·牛頓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