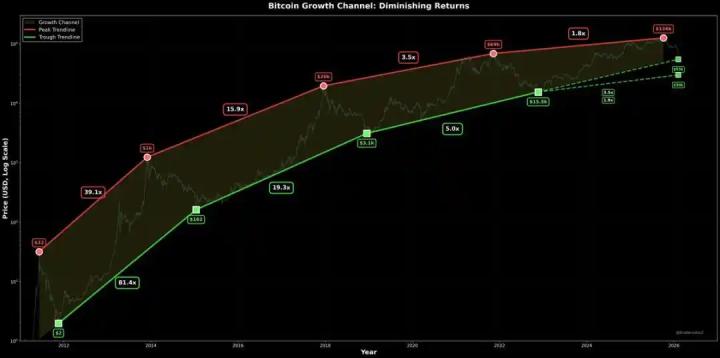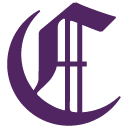我有幸與Rachel Janfaza聊了聊趨勢和數據——傳統妻子和新女老闆運動、年輕人和勞動力市場,當然還有社交媒體如何影響我們所有人。希望您喜歡這次對話!
這是一份由讀者支持的出版物。想要接收新文章並支持我的工作,請考慮成為付費訂閱者。
這幾天我都在山裡待著。越野跑是人生的絕妙比喻——躲避樹枝,跳過岩石,攀爬陡峭的山路,緩緩下降。一片寧靜,彷彿沒有雷鳴般的喧囂。
它給了我一些時間去思考。過去幾個月和幾周真是難以言喻。過去幾天,我把頭埋在鍵盤上,一遍又一遍地打出、刪除、再打出這句話,心裡卻不斷回想著這句話。
一天之內既發生了政治暴力事件,又發生了校園槍擊事件
吉米·坎摩爾 (Jimmy Kimmel) 在查理·柯克 (Charlie Kirk) 去世時說了一些(虛假的)話,並因此被停播,但根本原因是 (1) 特朗普希望他被停播 (2) FCC 威脅 ABC (3) 合併必須通過
Nexstar 旗下擁有數十家地方電視臺。現在,它想與擁有數十家地方電視臺的 Tegna 進行一筆價值 60 億美元的合併。要做到這一點,它必須與聯邦通信委員會 (FCC) 保持良好關係。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對 Kimmel 非常不滿,他在本尼·約翰遜的播客中明確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要麼幹掉 Kimmel 的節目,要麼 FCC 找你麻煩。
說到合併,剛剛完成 80 億美元合併的派拉蒙天舞公司正準備競購華納兄弟探索頻道,這將使 CBS 新聞和 CNN 合併。
TikTok 的出售定位旨在安撫中國,計劃出售給包括甲骨文和a16z在內的投資者集團,這可能使埃裡森家族得以廣泛進入媒體生態系統。特朗普已四次延長截止日期, 這是違法的。
超過300名韓國公民在佐治亞州現代-LG電池廠參與建設時被突襲逮捕(美國政府表示他們對此感到後悔)。這家美國急需的工廠要到2026年才能恢復運營。
因抵押貸款欺詐而試圖解僱美聯儲理事麗莎·庫克(結果發現其他人都在犯欺詐行為),並持續威脅美聯儲的獨立性
斯蒂芬·米蘭 (Stephen Miran) 被任命為美聯儲理事,同時暫時卸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一職,這引發了一個問題:他是否仍然同意自己在 2023 年發佈的關於獨立的推文?
年輕人的消費情緒持續低迷,加上自2024年以來青年失業率持續上升(因為人工智能減少了初級就業人數)。整體勞動力市場也在走弱(包括白領和藍領工作),同時通脹也在上升。
政客們越來越多地認定,他們的角色不是代表選民,而是成為社交媒體明星
尼泊爾政府被推翻,新總理通過 Discord 選舉產生
股市持續繁榮, 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最富有的 10% 的人現在佔總支出的近 50%
那麼,你該如何描述那些難以言喻的事情?你把它描述成一場考驗。所有這些故事——坎摩爾和聯邦通信委員會、派拉蒙和CNN、TikTok、米蘭在美聯儲、青年失業、特朗普支持率下滑——都是對機構的壓力測試。媒體能否抵禦被操控?央行能否保持獨立?政府能否維持信任?
我們正生活在信任、暴力和關注的危機交織之中,與此同時,物質條件卻日益惡化。這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人類對意義和確定性的掙扎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或許,這才是理解它的最佳方式。古老的神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這一切既荒誕又似曾相識。
雞和蛋
眼下的一個大爭論有點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社交媒體究竟是引發了問題,還是僅僅放大了更深層次的弊病——比如零和思維、制度崩潰和不平等?究竟是算法先行,還是絕望先行?
我覺得這很複雜。我相信“機器”的設計初衷就是將人類的注意力貨幣化,然後再賣給廣告商。而在以注意力為基礎的經濟中,憤怒是廉價的燃料,你可以把它扔進火裡,讓它燒得更旺更旺。真相、細微差別和分析是大多數人負擔不起的奢侈品——所以他們才會用“憤怒誘餌”來煽動憤怒。
與此同時,那些追逐大型併購案的公司卻選擇保持沉默,因為任何事(甚至法律!)都無法危及監管的青睞。你看,我的十億美元併購案必須通過。雖然獲得了關注,但獨立性也隨之喪失。
人們並非只是“被算法愚弄”。他們面臨著真正的壓力。 經濟正在疲軟。年輕人的生活重心截然不同,年輕男性和年輕女性之間的差異也持續存在。
前景黯淡將年輕男性推向高度精準的網絡生態系統,在那裡,經濟上的失望最終演變成文化上的不滿。焦慮創造了算法可以利用的心理條件。
人工智能也很奇特。平臺被那些可能並非出於好意的參與者控制(不斷改進Grok以迎合某種意識形態並不是什麼好事)。當機器成為某人世界觀的回聲時,它們究竟是為了誰?
所以是的:絕望與算法並存。為了解釋這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我認為我們需要神話。神話為我們提供了描述人類重複模式的語言,以及理解一切的框架。它們描述了和諧與不和、衝突與替罪羊、瘟疫與群體。書籍。
(1)Discord
米爾寇的不和諧之音愈演愈烈,之前聽到的旋律也淹沒在洶湧的聲波之中。—— 《精靈寶鑽》,JRR·托爾金
在《精靈寶鑽》的開篇,世界由埃努(Ainur)——神聖的神祇——歌唱而生,他們各自以和諧的聲音,譜寫出由一如·伊露維塔指揮的宏大交響樂章。然而,埃努中最強大的米爾寇卻將不和諧的音符引入了樂章。它混亂不堪,是一首充滿驕傲與暴力的旋律。當它融入造物主的肌理之中時,便會給世界留下永久的傷痕。
我們的世界也感受到了同樣的感受——秩序與混亂之間掙扎的時代。Discord(小寫的d,咳咳)已經成為一股核心的組織力量。在尼泊爾,Discord服務器(大寫的D)協調了推翻政府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而承載這起事件的鐵路也承載了查理·柯克兇手的供詞。
世界變得非常小,而平臺卻變得非常強大。社交媒體是一回事——我們都在信息流中互相叫喊——但私人聊天室對於理解互聯網的郊區化越來越重要。
熱門話題意味著數百萬人突然關注同一件事,在他們自己的算法宇宙中,無論是美國校園槍擊案還是國外的政治動盪。他們唱出不和諧的聲音,帶來動盪:半真半假、兩極分化、混亂。算法是參與的工具,許多人都知道這一切都是一場遊戲。為什麼不在創造的結構中唱出黑暗的歌聲呢?畢竟,這是賺大錢的好方法。
(2)責備
這段記載再次展現了模仿傳染的無所不能。彼拉多將耶穌交出,其動機是擔心暴亂。正如人們所說,他展現了“政治技巧”。這毋庸置疑,但為什麼政治技巧幾乎總是屈服於暴力傳染呢?——《 我看見撒旦像閃電般墜落》, Ren· 吉拉爾
不和諧的氣氛不斷出現。查理·柯克被殺,以及眾議員霍特曼和她的丈夫被殺——過去幾個月裡發生的兩起引人注目的政治暴力事件——都立即引發了政治化的反應。
對於柯克,有人要求以特定方式紀念他,司法部正在履行其職責。霍特曼眾議員沒有得到她應得的尊重,沒有降半旗,眾議員邁克·李還發了一條嘲諷的推文,配文“華爾茲街上的噩夢”,並附上一張殺害她的兇手的照片。
在這兩起事件中,死亡都成了黨派爭論的焦點。勒內·吉拉爾的擬態理論有助於解釋其中發生的情況。
人類的慾望是模仿性的——我們想要別人想要的東西(社交媒體的商業模式),當人們爭奪相同的慾望對象時,就會產生不斷升級的衝突。
這種模仿性的競爭不斷加劇緊張局勢,直至威脅到社區的分裂。
古老的解決辦法是尋找替罪羊:整個社區會一致將暴力行為指向一個(也許是無辜的)受害者,通過共同承擔責任來實現和平。
它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需要全體一致同意。
每個人都必須至少在公開場合就誰應該為他們的麻煩負責達成一致,而集體指責可以創造社會凝聚力,即使這種凝聚力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
但在網上,這種一致性在結構上是不可能的。同一悲劇事件會同時被完全不同的框架所解讀。謀殺成為了一種驗證既有世界觀和強化道德優越感的方式。數字替罪羊在信息流中放大了這種效應。悲劇成為了內容。
(3)永久人群
與許多人共同進行的謀殺,不僅是安全的、被允許的,而且確實是值得推薦的,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無法抗拒的。—— 埃利亞斯·卡內蒂,《人群與權力》
人群渴望滿足。卡內蒂認為人群是無限的,渴望擴張,具有感染力,能量包羅萬象。在他的世界裡,人群比我們現在看到的更具實體性——更多人聚集在一個廣場,只有一個目標。
如今,人群大多都在網上。數字人群永恆存在,無處不在,擁有壓倒性的力量。他們不需要公共廣場。他們總是在滾動瀏覽,總是在消化輸入的任何信息。
每當暴力事件爆發,你都能看到這種情況。無論是槍擊事件、抗議活動,還是其他什麼,都無關緊要。人群瞬間膨脹,這可以理解。有人譴責,有人歡呼,有人meme。同樣,算法不會區分譴責和慶祝,只區分純粹的參與。
卡內蒂認為,人群在散去之前,必須找到一種釋放,一種宣洩。但我們的數字人群從未真正消失。它不斷壯大,將一個故事串聯成另一個故事,形成一股持續的力量,卻從未迴歸個體。當人群永不回家時,政治會變成什麼樣?
(4)習慣
下定決心不再服役,你便立即獲得自由。我不要求你伸手推翻暴君,而只是要求你不再支持他。—— 拉博埃西,《論自願奴役》
人群可以膨脹,但也可能停滯不前。拉博埃西的觀點是,專制權力往往更多地依賴於習慣而非強制。人們習慣於服務、接受和規範化。他們並不會真正反抗,因為服從感覺上就像某種秩序。如果轉變過程足夠漸進,人們幾乎會接受任何事物。暴君並不總是需要鎖鏈。他需要的只是慣性。
但這其中還有更廣泛的應用。在一個便利已成為基礎設施的經濟中,獨立性的侵蝕令人感到熟悉。DoorDash 推出了“先買後付”的模式,人工智能減少了入門級工作崗位,政治變成了績效。人們接受侵蝕並非因為他們喜歡,而是因為抵抗令人精疲力竭。陷阱在於自願的奴役與效率共舞。
(5)宣傳
這種情況使得“時事人”很容易成為宣傳的靶子。事實上,這樣的人對當今潮流的影響高度敏感;由於缺乏參照物,他隨波逐流。他不穩定,因為他追逐今天發生的事情;他與事件產生共鳴,因此無法抗拒任何來自事件的衝動。由於他沉浸在時事之中,這種人存在一種心理弱點,很容易被宣傳者擺佈。—— 雅克·埃呂爾,《宣傳》
人群也會對噪音做出反應。埃呂爾認為,宣傳會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製造疲憊,最終侵蝕獨立性。這就像洪水氾濫之前的洪水氾濫。製造噪音,迫使人們調整行為以適應不確定性。你不必相信宣傳也能讓它發揮作用,你只需要調整自己去適應它的存在。這也有點像拉博埃西的觀點——權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永不抵抗。
我們的媒體整合環境開始呈現這種局面。派拉蒙和天舞影業正在爭奪華納兄弟探索頻道,這筆合併將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頻道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納入同一屋簷下。甲骨文可能也對TikTok有所涉足。Nexstar正在爭取Tegna,但這取決於FCC的批准。每個人都知道該如何玩這個遊戲——討好、做該做的事情、賺取數十億美元、犧牲前人為之奮鬥的成果等等。
埃呂爾會說,危險在於那些未說出口的話,即自我審查。飽和效應使人們變得謹慎、沉默、猶豫。它縮小了言論空間,甚至不需要正式禁令。人們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所以像ABC的高管一樣,選擇退縮而不是採取報復行動。
如果宣傳通過毒害氣氛來發揮作用,那麼當我們的氣氛被沉默所主導時會發生什麼?
(6)電源
我們所說的人類對自然的力量,實際上是一些人利用自然作為工具,對其他人施加的一種力量。—— CS Lewis,《廢除人類》
沉默最可怕。劉易斯警告說,當價值觀被掏空時,機構就有可能被原始意志所掌控。他稱之為“道” :對是非對錯的共同理解,是所有人類價值觀和機構宗旨的基礎。一旦這個框架被掏空,支配就會隨之而來。操縱權力槓桿的人會操縱這臺機器,使其朝著自己的目的發展。
央行的設計初衷是作為獨立的緩衝,是貨幣穩定的中立仲裁者。然而,特朗普任命的官員之一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如今卻在離開白宮另一份工作的同時,擔任美聯儲理事——他曾批評萊爾·佈雷納德(Lael Brainard)擅自闖入這扇旋轉門。他還相信這一點嗎?還是說,獨立本身已經淪為一場鬧劇,一場中立的表演,而非中立的實踐?
媒體也是如此。新聞業的根基在於追求真相。失去真相,一切就會變得混亂。媒體變成了控制發行權者的容器,無論是派拉蒙/Skydance/a16zTikTok,還是擁有否決權的監管機構。
劉易斯的警告是,當機構忘記其存在的意義時,其權力的本質就會被攫取。技術、監管和專業知識都會成為意志的工具。屆時,情況就會變得危險。機構還記得它們的使命嗎?一旦失去了“為什麼”,其本質就會被扭曲成任何樣子。
最後的想法
問題在於社交媒體究竟是導致絕望,還是僅僅放大了它。就像我們咖啡店裡有機器人在運營互動農場一樣。我們目前的經濟建立在憤怒之上,而政治體系則旨在滋養這種憤怒。所以答案是兩者兼而有之。它放大了既有的東西,並在此過程中重塑了未來。
我們真正面臨的是一場更廣泛的考驗。機構能否牢記自己的使命?媒體能否抵禦被操控?監管機構能否保持獨立?政府能否維繫信任?還是說,習慣、宣傳和空洞的價值觀會將它們變成純粹權力表演的舞臺?
這些書提醒我們,這種不確定性並非首次存在(有人可能會說它一直存在),而且很可能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用最戲劇性的話來說,崩潰並非源於挑戰,而是源於應對。
這是一份由讀者支持的出版物。想要接收新文章並支持我的工作,請考慮成為付費訂閱者。
謝謝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