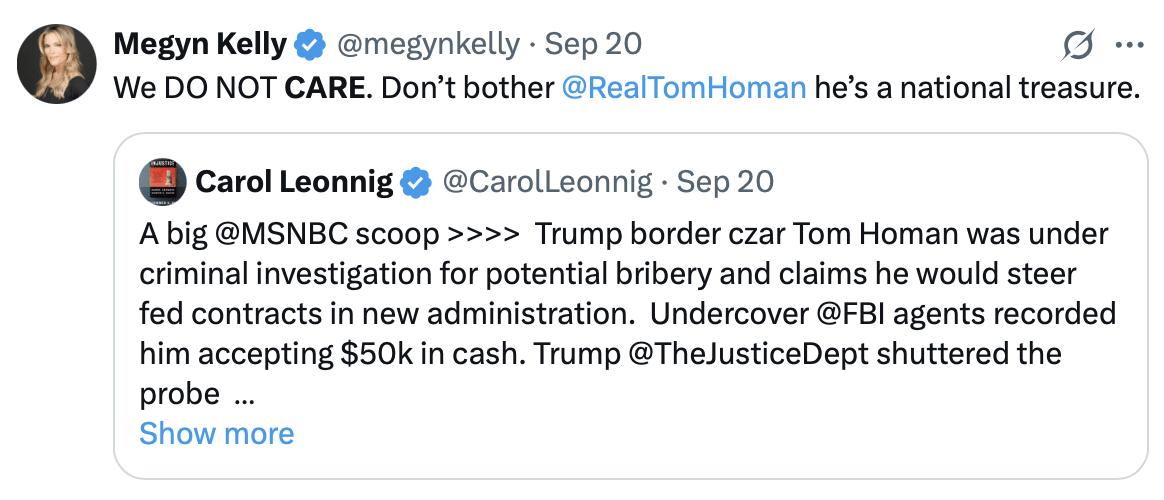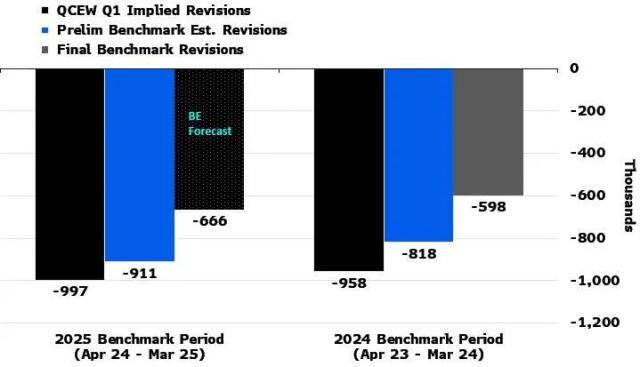早上好!
這是一份由讀者支持的出版物。想要接收新文章並支持我的工作,請考慮成為付費訂閱者。
現在幾乎不可能不被新聞淹沒。上週我參加了一場婚禮,每次談話最終都會回到同一個話題:我們身處的世界以及正在發生的一切。感覺地球移動的速度快得讓人難以跟上。
有些人認為這種轉變是進步,另一些人則認為是崩潰。無論如何,數字生活與現實生活之間的界限正日益模糊。網上發生的事情就是現實生活。我們消費什麼,我們就會成為什麼。
許多思想家都曾探討過這個問題——波茲曼、德波、赫胥黎、奧威爾探討媒體;馬基雅維利、托克維爾、修昔底德、吉本探討不確定時期的人性腐敗。無盡的信息與煽動性經濟的融合,為我們理解世界和理解彼此的方式的分裂創造了完美的環境。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我們不再相信機構能夠提供真相、公平或流動性。它們曾經是幫助我們從原始數據攀升至智慧的腳手架。而當這些腳手架失效時,人們就會適應:一些人在地位競爭中表現出色(因為不得不如此),而另一些人則完全背棄義務(如果機構對我不起作用,我為什麼要為它們工作)。
混亂的建築
有幾種方法可以描繪我們扭曲的信息生態系統。
DIKW 金字塔(數據 → 信息 → 知識 → 智慧):底部是原始帖子和點擊,中間是熱門內容,上面是共享的真理,最後是智慧,即看到原因而不僅僅是症狀的罕見能力。
或者說是“推理階梯”:我們從數據出發,賦予意義,做出假設——而我們的信念往往會影響我們選擇的數據。機器人和算法劫持了這層“階梯”,在我們還沒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之前,就將我們推向了兩極化的信念。
綜合起來,我們可以將它們組合成所謂的信息層次結構:
原始數據:源源不斷的帖子、點贊、機器人垃圾郵件
信息:標題、標籤、熱門話題
知識:我們分享和爭論的故事。
理解:認識到什麼可能不是真實的(或超真實的)
智慧:系統分析,能夠發現原因而不僅僅是症狀。
現在,我們被困在等級制度的中間層:淹沒在憤怒之中,為黨派熱點問題爭吵不休,很少能達成理解,幾乎從未獲得智慧。
混亂總有其製造者。如果我們想理解當今的美國民主,就需要了解這些製造者是誰,以及他們如何從混亂中獲利。
媒體集中作為基礎設施
這種兩極分化源於媒體集中度。 1996年《電信法》的宣傳口號是加強媒體和電信領域競爭,但實際上卻適得其反。五年內,四家公司控制了美國約85%的電話基礎設施。這項放松管制的舉措支撐了如今整個媒體環境的整合——不僅僅是電話,還包括報紙、社交媒體和電視臺。
媒體所有權日益集中,注意力日益金融化,信息從公共產品轉變為可供買賣和操縱的私人商品。
例如,拉里·埃裡森正在打造一個相當龐大的帝國。他的兒子正在管理新合併的派拉蒙-天舞影業, 他們可能會競購華納兄弟探索頻道,從而控制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頻道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派拉蒙的合併是在他們執行特朗普的命令並解決了1600萬美元的訴訟後才得以完成的。
埃裡森還是一個投資者財團的成員(該財團還包括福克斯新聞的所有者默多克家族),該財團可能擁有TikTok 。如果埃裡森的交易成功,他將控制擁有超過2億訂閱用戶的流媒體服務(包括Paramount+和HBO Max/Discovery+)、一個主要的廣播電視網絡和新聞部門(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一個頂級有線新聞網絡(CNN)以及全球最大的社交網絡之一(TikTok)。
這為什麼重要?因為控制大眾傳播手段就意味著控制敘事。這是注意力經濟版的壟斷。當一個人(或少數精英)掌控報紙、電視臺和社交媒體平臺時,其他聲音就毫無存在空間了。
但有點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息生態系統。埃隆·馬斯克擁有推特,他利用推特幫助特朗普贏得了2024年大選。傑夫·貝佐斯擁有《華盛頓郵報》,並已開始變得更加包容。馬克·扎克伯格控制著一個社交應用帝國,並多次面臨算法偏見的指控。
當信息就是力量,注意力就是貨幣時,最有錢的人當然會試圖購買最大的影響力。通常情況下,像聯邦貿易委員會這樣的機構會說:“嗯,我不認為一個人應該對信息環境擁有超乎尋常的控制權”,但現在情況並非如此。白宮正樂於將監管手段武器化。
特朗普公開威脅要吊銷批評他的電視網絡的廣播執照。邏輯很簡單:想保住執照?那就說些總統的好話。想降低關稅?那就承諾外國直接投資。需要簽證折扣?那就做個交易。就像德里克·湯普森說的,這完全是奉承經濟學。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布倫丹·卡爾 (Brendan Carr)因吉米·坎摩爾 (Jimmy Kimmel) 對查理·柯克 (Charlie Kirk) 悲慘死亡事件發表不敏感的評論而將其驅逐,並計劃如果其他人不播放合適的船伕號子來紀念政府,他們也將遭到驅逐。
吉米·坎摩爾 (Jimmy Kimmel) 確實被撤下,但在損失了數十億美元之後,美國廣播公司 (ABC) 很快又將他重新啟用。
然而, 兩家當地廣播集團Nexstar(他們想要完成一項價值 60 億美元的合併!)和 Sinclair 都不會播放 Kimmel。
布蘭登·卡爾 (Brendan Carr)表示,這一切的發生都是因為吉米·坎摩爾的收視率,而不是政府。但特朗普隨後在“真相社交”節目中說道:
“我們要試試ABC的招數。看看效果怎麼樣。上次我去找他們的時候,他們給了我1600萬美元。這次聽起來更賺錢。真是一群失敗者。”
所以,政府顯然參與其中了。這是一個糟糕的局面。讓特朗普贏得選舉的媒體環境——尤其是像JOE·羅根這樣的播客——已經公開反對這種做法。
JOE·羅根: “如果政府試圖讓吉米·坎摩爾噤聲,是因為他們試圖推動某種合併,而特朗普不喜歡吉米·坎摩爾,那麼這件事就應該被揭露。”
但事情的真相顯而易見。言論自由就是政府認為不覺醒或類似的東西。這就像垂直的“取消文化”——一種國家與首都的混合體,平臺和政客互相利用,以懲戒異見。
即使你同意政府的做法,但有一點越來越明顯:我們的大眾傳播系統日益私有化,並且以利潤和權力為目標,而不一定是為了真相或公共利益。
在吸引注意力就等於收入的環境中,這些人有動力讓交流變得更加令人上癮和聳人聽聞——這對公共討論來說從來都不是好事。
紅色與藍色
我們信息系統的斷裂在美國內部體現得最為明顯。彭博觀點專欄作家羅納德·布朗斯坦稱,特朗普的“訴訟、資金威脅和軍隊使用”正在導致紅州和藍州之間的分歧日益擴大,這是“自內戰以來對國家凝聚力的最大壓力”。忠誠度正在從憲法轉向球隊顏色。
著名保守派評論員梅根·凱利表示,她並不關心特朗普的邊境事務主管湯姆·霍曼收受了 5 萬美元的賄賂。
她之所以不在乎,部分原因可能是現在每個人都逍遙法外。如果你能討好特朗普,美國機構的重擔就能全部卸下來。如果你惹怒了他?你就會被徹底擊垮。法治變成了衡量忠誠度的尺度。
正因如此,憤怒才成為美國最可靠的出口。特朗普對聯合國說,他們的國家“正在走向地獄”。這當然是一種侮辱,但也表明了:我們的國家品牌就是怨恨。
但令人悲哀的是,這不僅關乎物質,也關乎文化。穆迪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警告稱,美國三分之一的地區已經陷入衰退。這種經濟壓力只會加深裂痕,讓雙方各自對正在發生的事情和責任歸屬形成“真相”。
在經濟問題面前,文化戰爭本應顯得微不足道,但卻變得更加激烈。
國際鏡報
國內發生的事與國際舞臺上的情況如出一轍。特朗普對待國際機構的態度是退縮、蔑視,以及對共同框架的蓄意破壞。再說一次,即使你認同他的政策,這客觀上也是他正在做的事情。
安德烈亞斯·克魯斯 (Andreas Kluth)將其描述為“全世界都擔心外交官們所說的‘國際社會減一’的命運”。曾經建立這些體系的國家現在卻致力於摧毀它們。
同樣的邏輯也在國內造成分裂——(1) 認為合作(或至少是表面上的合作)是軟弱;(2) 認為共享機構是障礙而非工具。當人們對共享機構失去信心,當他們無法就基本事實或共同程序達成一致時,他們就很容易被任何擁有足夠金錢或技術來填補這一空白的人操縱。
注意力會流向奇觀,而奇觀會獎勵那些願意破壞而不是建設的人。所以人們會尋找替代方案。 中國正在增加黃金儲備,大概是為了實現去美元化。其他國家或許更喜歡這種選擇,而不是一種由充分信任和信用支撐的法定貨幣,而目前這種貨幣缺乏足夠的信任和信用。
新的權力結構
其他國家也通過極其高效的市場操縱策略對美國施加影響。我們這裡存在機器人問題——從經濟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會有所幫助。
機器人本質上是一種低成本、高槓杆操縱信息市場的方式。其商業模式非常巧妙:只需在虛假賬戶和自動化方面進行少量前期投資,就能在關注度、敘事控制力以及最終的政治成果方面產生巨大的回報。
2010年美國中期選舉期間,研究人員發現機器人被用來支持某些候選人並抹黑對手——數千條鏈接到虛假新聞網站的自動推文被注入政治辯論。即使在當時,ACM也警告稱,此類活動可能“通過影響選舉結果來危害民主”。 因為選民可能會被表面上的公眾情緒高漲所左右。
機器人在 2016 年大選期間真正進入公眾意識,當時研究人員發現,僅 6% 的 Twitter 賬戶就傳播了 31% 的所有低可信度新聞(詳見優秀論文《社交機器人傳播低可信度內容》)。他們的策略是儘早放大,製造虛假共識,然後讓人類心理學完成剩下的工作。
正如該論文作者之一Giovanni Luca Ciampaglia所說:
人們往往更信任那些看似來自多人的消息。機器人利用這種信任,讓消息看起來非常受歡迎,從而誘騙真人為其傳播消息。
這是典型的市場操縱策略,但因注意力經濟而有所調整。相對較少的機器人操作員可以利用決定哪些內容能被曝光的網絡效應,製造社交媒體的“現實”。根據《社交媒體效應:劫持公民參與中的Civic與文明》報告,2016年,關於主要候選人的推文活動一度高達20%至33%,這些推文並非來自真正的支持者,而是來自機器人或傀儡賬戶(由真人運營的虛假賬戶)。
自此以後,機器人就一直是網絡討論的焦點。一篇名為《社交媒體機器人與人類特徵的全球比較》的論文對此進行了詳盡的闡述:
在 2020 年美國大選中,分析人士再次發現機器人網絡“積極歪曲或捏造敘事,以製造兩極分化的社會”。
在 COVID-19 疫情期間,機器人大軍在社交媒體上積極傳播反疫苗言論和陰謀論
人們還發現,機器人通過推動極端主義運動(例如,擴大 QAnon 的影響)來推動極端主義運動,從而招募更多偶然發現它的人類追隨者。
投資回報率非常高。只需花費幾臺服務器和一些編程人才,外國對手就能影響美國大選,國內極端分子就能將陰謀論推向主流,商業利益就能操縱公眾輿論,從疫苗到氣候變化,無所不包。全球網絡流量分析反覆發現,機器人(無論好壞) 佔據了超過一半的互聯網流量。研究表明,近60%的用戶通常無法區分機器人和真人。
當製造共識的成本低廉,並且對那些從混亂中獲益的人來說很有價值時,你就得到了工業規模的操縱。
我們生活在一個投機經濟時代,感知比基本面更能驅動價值。看看股市: Nvidia 憑藉 OpenAI 1000 億美元的投資(OpenAI 將用這筆錢購買更多 Nvidia 芯片),市值上漲了 1500 億美元。十家公司之間數千億美元的資金來來回回,標準普爾指數就像在衡量某種真實的東西一樣飆升。
都是穿西裝的表情包。meme股票和Dogecoin至少以前看起來像笑話;現在,同樣的投機能量貫穿了企業核心。關注度、認知度和敘事比產量或利潤更能推動估值。
顛倒的層級結構
我們構建了一個信息層次完全顛倒的世界。
在底層,機器人用原始噪音淹沒我們。在中層,憤怒和團隊敘事被固化為“知識”。在頂層,通往智慧的階梯,比如新聞、學校、Civic話語、共享機構,都被削弱了。曾經幫助我們攀登的腳手架已不復存在。
傳統的解決方案——事實核查、媒體素養、內容審核——都假設我們面對的是內容問題,而實際上我們面臨的是基礎設施問題。你無法通過事實核查來擺脫一個旨在獎勵虛假信息的體系。你無法通過教育來繞過那些為兩極分化而優化的算法。你無法通過審核來擺脫那些讓混淆視聽從其利益的經濟激勵。
認識到這是一個市場結構問題而非信息問題,一切都會改變。與其關注個別不良行為者或具體的虛假聲明,不如開始思考那些讓操縱既有利可圖又可擴展的底層系統。
信息戰是經濟政策,它決定了我們如何分配注意力、構建激勵機制以及如何組織信息流,而這些信息流又影響著我們做出的每一個市場和政治決策。我認為在 Substack 上就此發表長篇大論沒什麼用——但我們需要認真對待 (1) 媒體的力量,以及 (2) 那些試圖影響媒體力量的人。有辦法登上信息層級的頂端!我們不必被困在這些中間層。
這是一份由讀者支持的出版物。想要接收新文章並支持我的工作,請考慮成為付費訂閱者。
謝謝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