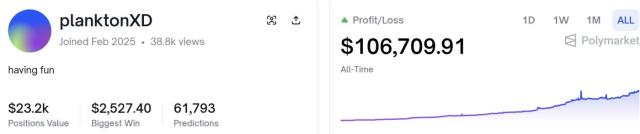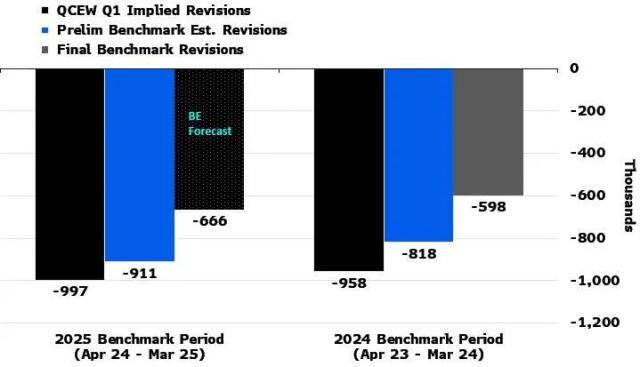“文明的重大進步幾乎摧毀了其所處的社會。”—— AN Whitehead
當肖恩·阿切爾和卡斯特·特洛伊互換面孔,重獲新生時,他們體現了成為“他者”的生存困境。阿切爾努力應對特洛伊惡行帶來的混亂自由,而特洛伊則沉醉於阿切爾井然有序的家庭生活。
這種反轉表明身份是表演性的,由環境和選擇而非天生的本質所塑造,當每個人面對內心的陰暗自我時,善與惡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最終意味著復仇和救贖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交換的面孔代表著掩蓋更深層真相的欺騙性陰影;人物的旅程迫使人們去思考真實性與外表,強調社會角色、個人創傷和野心如何禁錮靈魂。
所有通過規範強加的角色,都是一座囚禁人類意志的牢籠。然而,它們也為社會的正常運轉提供了穩定性。意志最終掙脫束縛,帶來混亂,最終重建穩定,這始終只是時間問題。
容器:加密身份危機
我開始相信,技術是社會運作的基礎。技術創造了一個幾乎看不見的環境,一個網絡,它就像一個劇院,有其自身的物理規則和其他更抽象的規則。
我第一次接觸加密貨幣是在2016年讀到以太坊白皮書的時候。對我來說,這是人類社會治理方式的根本性變革。後來我讀到了Nick Szabo關於社會可擴展性的思考,它全面地反映了我零散的思考。
在當今的話語中, 區塊鏈被簡化為數據庫解決方案,信任最小化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每個人都追逐金錢,但在這種情況下,金錢卻將我們引向死衚衕。我們正在逐漸削弱信任最小化的要求,首先是為了性能,然後是為了用例,最終是為了迎合政府和企業增加購買量的需求。
如果加密貨幣是一部電影中的角色,那麼它將是一個技術無政府主義毒販的故事,他通過從華爾街交易員轉變為科技創始人的可卡因職業生涯,成為在漢普頓度過夏天的摩根大通董事會成員。
兩個主要的梗概括了加密貨幣當前的情緒。一個是“相信某事” ,這本質上反映了加密貨幣無法對其想要實現的目標有一個確定性的看法。“某事”應該理解為“無事” 。價格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meme是“實用主義至上” 。中心化鏈、單一排序器、性能優化、審查合規等等。實用主義正在慢慢蠶食加密貨幣真正的獨特賣點——信任最小化,從而實現社會可擴展性。換句話說,就是減少對可信第三方的依賴。
革命似乎真的吞噬了它的孩子們。早期的革命者變得過於富有,無暇顧及這些,如今他們卻讓人想起了他們曾經反抗的銀行家。2021年關乎法國在另類金融軌道上的未來,而2025年則關乎如何將信任最小化的機器包裝成信任最大化的工具,併為空談找到願意購買的人。
的確,這完全是一場權衡利弊的遊戲。我們不能成為去中心化至上主義者,因為那不切實際,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商業化。當鐘擺擺得太過偏向中心化時,我們應該意識到,去中心化的意義已經蕩然無存,我們兜售的只是金融化的虛無。換句話說,金融化的金融化。為了收益而收益。
這將加密貨幣定義為一種可以買賣的載體,一種超金融化的手段。但加密貨幣不僅僅是一種載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誤解了。加密貨幣是一種環境。
回到本節的第一段,社會運作的基礎已經改變,而且沒有回頭路了。
環境:電氣劇
加密貨幣將不可避免地吞噬我們今天認為的一切使其得以存在。它不是一個容器—— “股票,而是鏈上” 。它絕對是一個全新的環境。它是市場的延伸和轉型,是我們參與其中的無形環境。我將引用麥克盧漢的觀點來闡明這一點:
新舊環境的相互作用造成了許多問題和困惑。我們難以清晰理解新媒體的影響,最大的障礙在於我們根深蒂固的習慣,即從固定的視角看待一切現象。
麥克盧漢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預見到,印刷技術創造了公眾,而電子技術創造了大眾。他知道無形的環境正在改變,社會也在改變,但他也注意到,官方文化正在努力迫使新媒體去做舊媒體的工作。
我們不能指望那些生存依賴於舒適地前進的舊進程的個人和當局能夠看到新環境的實質或理解其性質。
詩人、藝術家、偵探——任何能讓我們感知敏銳的人,往往都是反社會的;他們很少“適應良好”,無法順應潮流和趨勢。反社會類型的人之間往往存在著一種奇特的聯繫,他們能夠洞察環境的本質。
這種需要與某種反社會力量交織、對抗環境的需求,在著名的故事《皇帝的新衣》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適應良好”的朝臣們擁有既得利益,認為皇帝裝扮得漂漂亮亮。而“反社會”的頑童,不習慣舊環境,清楚地看到皇帝“一絲不掛”。新的環境對他來說一覽無餘。
因此,加密貨幣發現自己在有意識地徒勞地嘗試融入其中,而在無意識中,它卻創造了一個新世界,人們正在緩慢但堅定地選擇加入其中。雖然該行業急於為這些一致性機器提供資金,但少數用戶默默地表示反對,遵守新媒體的規則。
年輕人本能地理解當下的環境——電子戲劇。它活得充滿神話色彩,且深刻深刻。這正是代際疏離感嚴重的原因。戰爭、革命、民間起義,都是電子信息媒體所創造的新環境的交匯點。
加密貨幣的真正普及並非源於優化,而是源於參與的渴望。任何人都可以成為銀行家,我們可以爭論銀行和銀行、銀行家和開發者之間的界限。
互聯網領域,尤其是加密貨幣領域,將教育過程從“打包”轉變為“發現” 。指導不再重要;手冊已經過時。麥克盧漢曾暗示,人們拒絕目標,渴望角色。他們渴望參與。如果說這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如此,那麼今天就更是如此。
我們的技術迫使我們過著神話般的生活,但我們的思維卻依然支離破碎,停留在單一、分離的層面上。神話意味著將自己置於觀眾、置於環境之中……”
面朝上
秉承《變臉》的精神,加密貨幣也面臨著自身的身份危機。真正以信任最小化、增強社會可擴展性的環境,正受到普遍的實用主義或價格行為的挑戰,這些因素使其淪為純粹的金融工具。
正如肖恩·阿切爾 (Sean Archer) 和卡斯特·特洛伊 (Castor Troy) 被迫生活在彼此的世界一樣,加密貨幣的先驅者們現在正在努力應對他們試圖顛覆的系統,他們往往採用中心化和信任最大化的傾向,從而奪走他們的真正實質和 USP。
加密貨幣作為一種環境與一種載體之間的張力,映射了電影的核心主題:真實性與表象,以及革命與同化之間模糊的界限。這如同“欺騙性的陰影”,掩蓋了加密貨幣更深層次的真相,就像《變臉》中交換面孔掩蓋了真實身份一樣。
然而,正如麥克盧漢所描述的那樣,加密貨幣的“電光火石”仍在不斷上演,超越了將其強行納入舊範式的嘗試。儘管官方文化,包括加密貨幣行業本身的大部分內容,都在努力讓新媒體完成舊媒體的工作,但少數用戶卻在無意識地、默默地持反對態度,選擇進入一個建立在不同規則之上的新世界。
這些“反社會小子”不適應舊環境,或許隱隱覺得皇帝根本無能為力。他們代表著推動加密貨幣真正普及的參與和投入,拒絕單純的優化,而是選擇與互聯網世界進行一種全新的、神話般的互動,讓每個人都能掌控一切。
歸根結底,選擇加密貨幣,就像 Archer 和 Troy 的選擇一樣,關乎對真實性的考量,以及對其變革力量的擁抱。這關乎理解加密貨幣不僅僅是一種“鏈上股票”或數據庫解決方案,而是對社會底層的根本性變革。
一個存在、思考、創造和參與的新環境。
感謝Lachlan和longsolitude的反饋。
感謝您閱讀《Wrong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