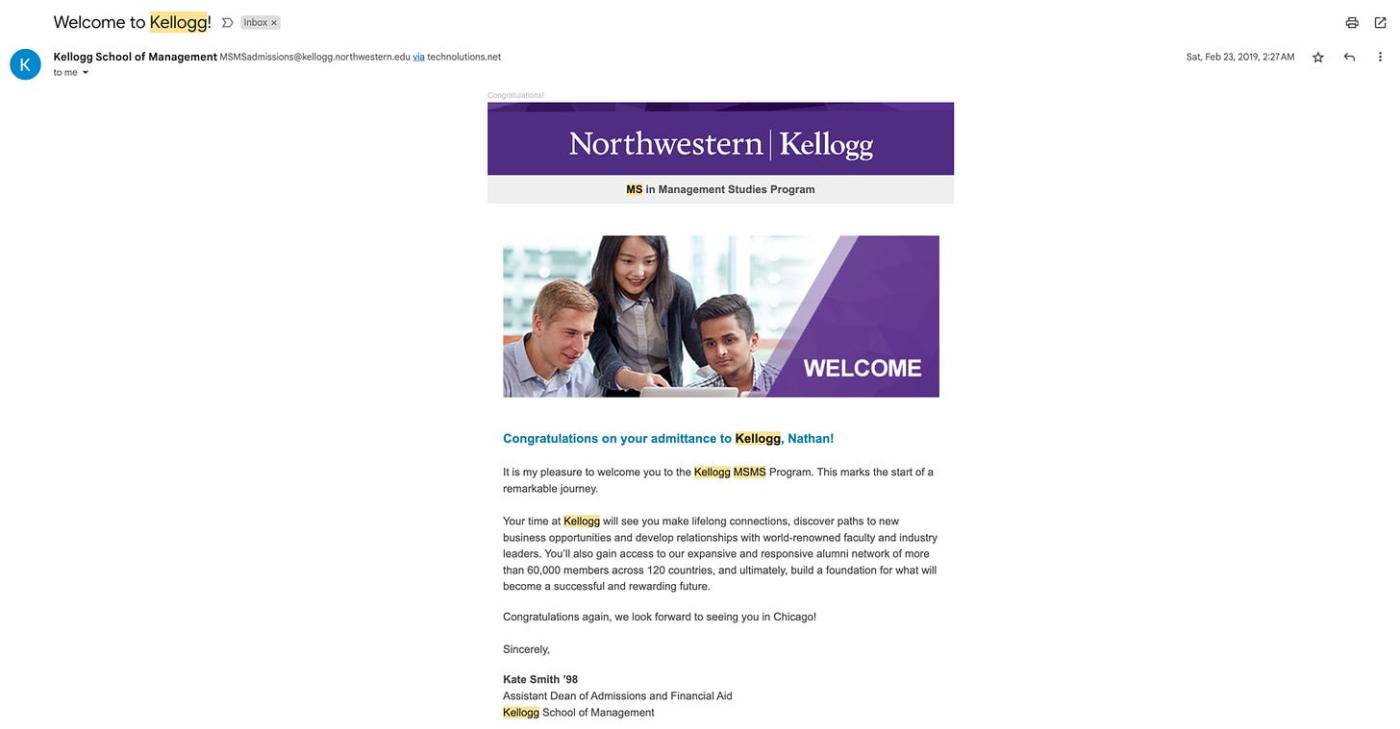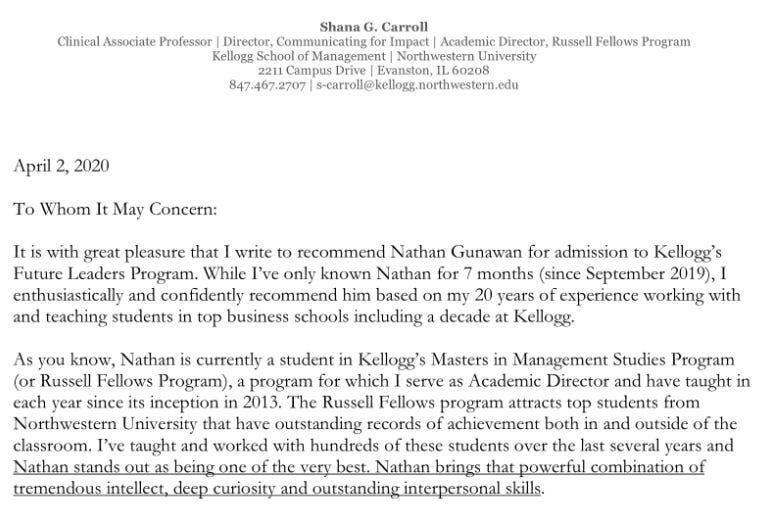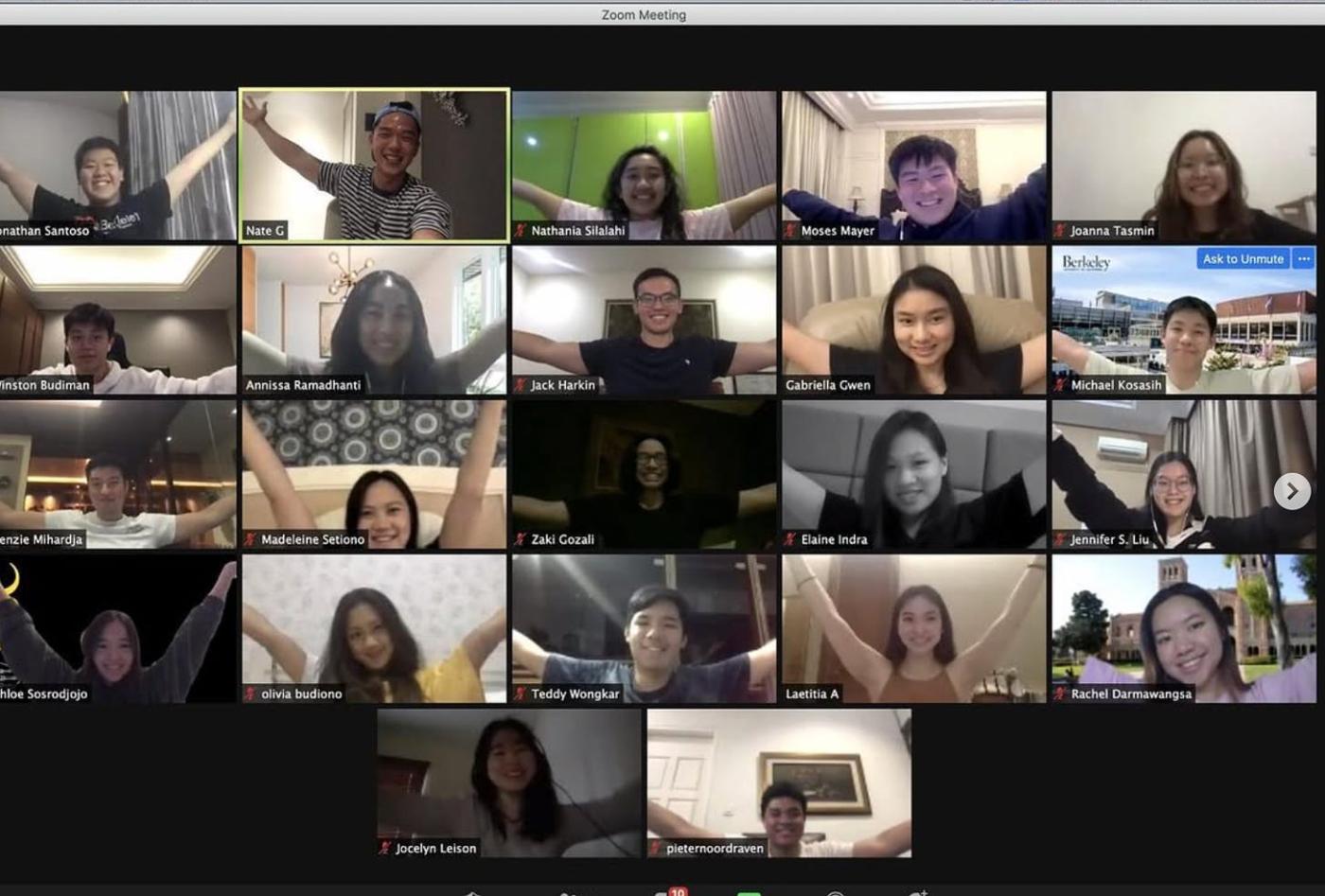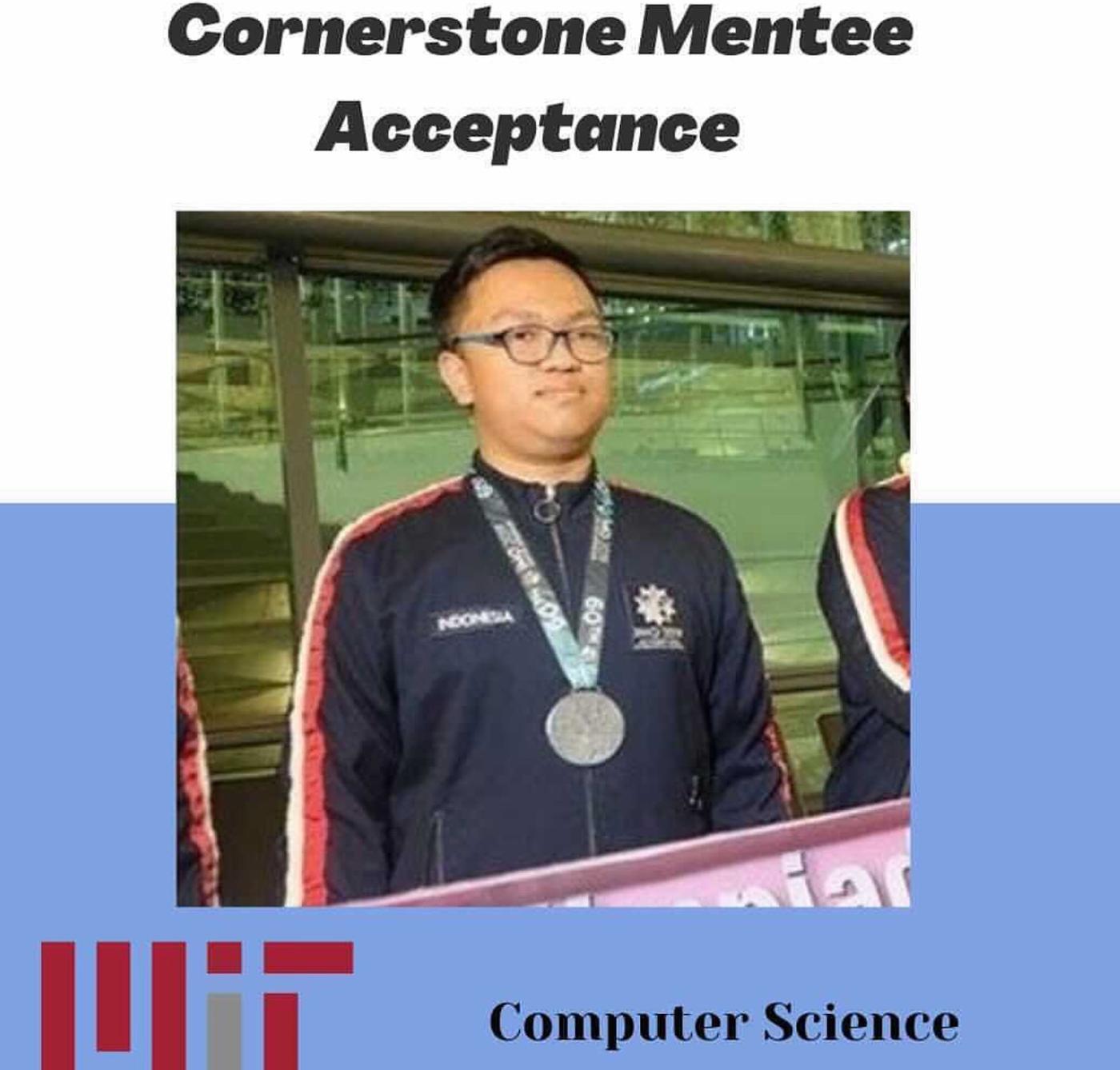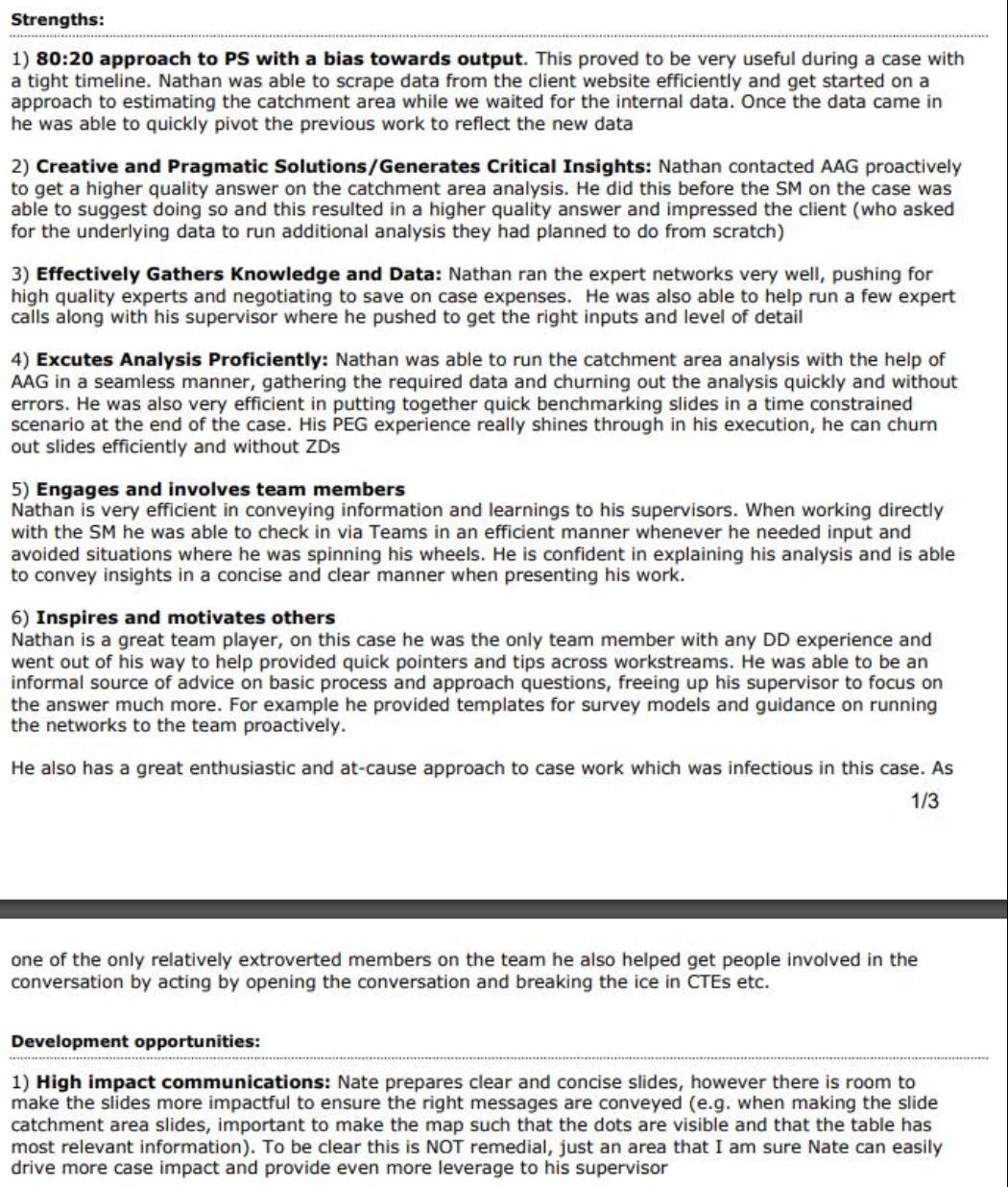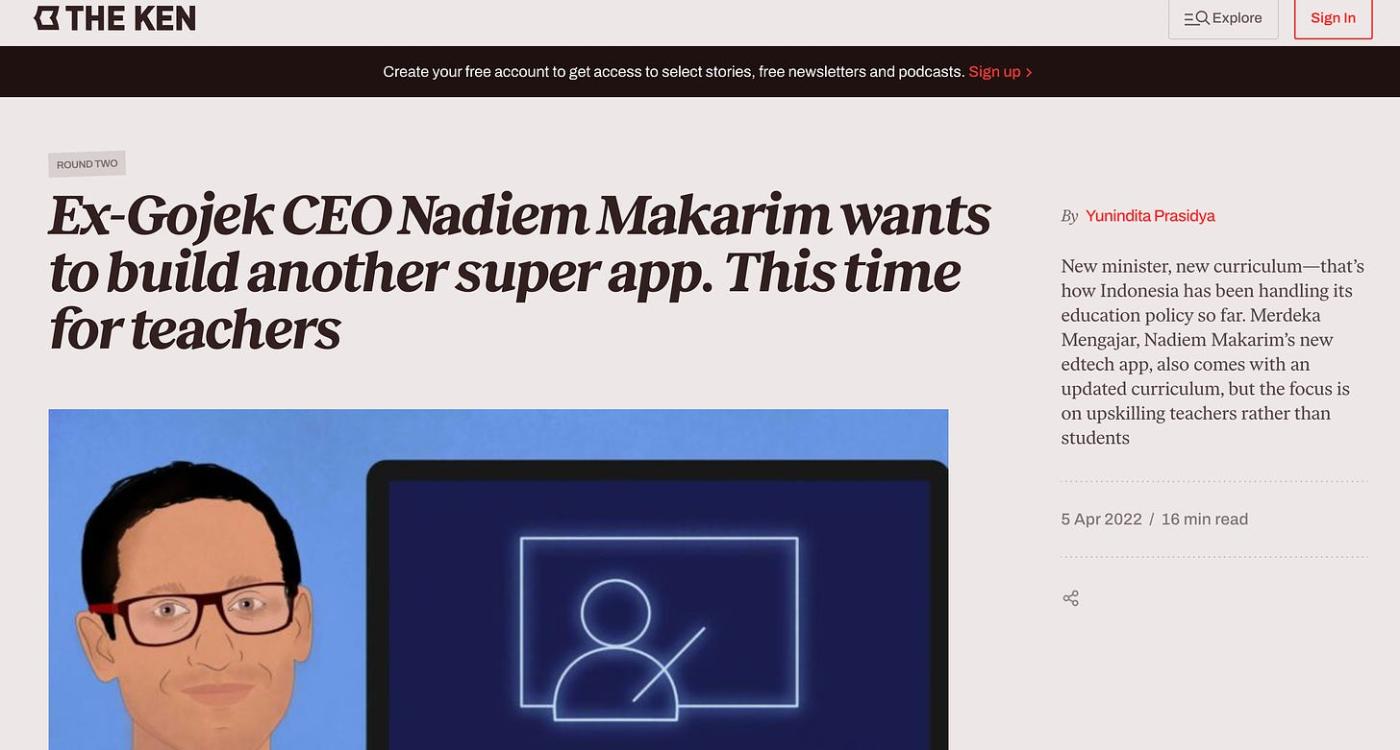簡介和目的
大家好,我叫 Nathan Gunawan,是 Pallav Technologies 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通常我的個人業務介紹就到此為止了。也許會稍微詳細地介紹一下我的教育或工作經歷。但只會再多花 20-30 秒。
最近,我注意到年紀大一些、資歷更高的人會放慢速度:對個人背景更加好奇:我的家庭、我在哪裡長大、我的愛好、我的個人“最終目標”。這讓我想到:大多數人很少問我這些問題,但也許這些問題才是真正重要的。
從投資者或長期業務合作伙伴的角度來看,這有點奇怪,不是嗎?你信任重要的資本來源——金融、社會、專業——卻不知道對方到底是誰。但證據表明,深入瞭解個人才是最重要的。
最瞭解這一點的人。例如,他們知道大多數初創公司都會轉向並過渡到與最初不同的領域,而創始人的韌性和好奇心使他們能夠繼續前進,走向更好的境界。
這就是為什麼 Hummingbird 尋找的是特殊的創始人(“獨特的童年創傷”)。這就是為什麼像 20VC 的 Harry Stebbings 這樣的人不斷強調早期投資的“誰”的本質。
作為一名創始人,這讓我開始思考。我可能沒有太多時間與大家分享我的深刻個人故事。投資者在實時盡職調查期間要求坦誠相告也並不總是一件舒服的事。那麼,與其私下談論,我為什麼不直接公開分享我的故事呢?除了表面的事實,我還可以更詳細地寫下表面之下的事情: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無論是好是壞。
最好的投資者和商業夥伴會檢查他們能接觸到的一切。有人告訴我,我的 Substack 文章(例如關於金融科技的文章)有助於讓投資者對我的金融服務知識充滿信心。
最好的情況是,這個故事可能會吸引那些與我迄今為止一生所建立的價值觀產生共鳴的人。而且沒有最壞的情況——這只是我生活中的事實!所以讓我們深入挖掘吧。
幼兒期和移居新加坡
我於 1997 年 9 月 4 日出生在雅加達。在我的記憶中,這是一個普通的童年,幸好沒有太多的痛苦或煩惱。我媽媽瑪麗亞是全職媽媽,我爸爸查爾斯是一名金融專業人士,在印度尼西亞一家當地銀行擔任投資銀行家。
我童年時期有兩個重要的催化劑動搖了當時的“平凡生活”。
第一個催化劑是我姐姐妮可的出生,2003 年,當時我 6 歲。不幸的是,妮可出生時患有一種罕見的疾病,稱為慢性嘔吐綜合徵,這對她的日常生活不利。當時,這種疾病尚未得到很好的理解,因此很難治療。這意味著她會經常“發作”,在此期間她會不斷嘔吐,有時一天會嘔吐 20-30 次以上。發作期間,她必須去醫院接上靜脈滴注。許多事情都會引發發作,但其中一個潛在原因是空氣汙染(我們都知道雅加達的空氣汙染就是這種情況)。
第二個催化劑是我父親事業的加速發展。我八歲時,他被聘為董事總經理,負責領導高盛的印度尼西亞戰略。從 2005 年起,他正式受僱於新加坡,工作地點也更多地在新加坡(儘管他的大部分發起工作仍在印度尼西亞)。
這兩個催化劑相遇,2006 年,我 9 歲,家人決定趁著爸爸獲得就業準證的機會移居新加坡。那裡的醫療條件和氛圍對我妹妹來說會更好。從一開始,事情似乎會變得更好。
我很快就適應了新加坡的生活。我爸爸把我送到新加坡美國學校學習(我媽媽最初很懊惱,她想讓我去新加坡當地的學校)。我爸爸的理由很明確:美國人更全面、更外向,單靠智力並不能取得成功。那時我還是個害羞、內向的孩子。因此,在美國學校環境中成長會面臨更大的挑戰。雖然在開學的頭幾個星期我的手臂骨折了,但我還是很好地適應了美國的環境。我讀了很多書(養成了終生的習慣),參加了更多的體育運動,變得更加善於交際和富有想象力。
與此同時,我姐姐的病情也慢慢好轉了。我們一家人發現治療方法開始見效,她的病情開始逐漸減輕:雖然緩慢,但確實在逐漸好轉。
與此同時,我父親的事業不斷發展,最終於 2008 年擔任瑞士信貸印度尼西亞分行的地區主管。我 11 歲時,我父親回到印度尼西亞,而我的家人決定讓我媽媽、姐姐和我留在新加坡。這個決定將成為我人生下一階段的催化劑。
父母離婚與抑鬱
由於我爸爸的工作和家人決定留在新加坡,我爸爸最終不得不接受我現在才真正理解的作息時間。他平日會留在印度尼西亞,週五則飛回新加坡,與家人共度週末。
“想象一下,睡眠不足,你只想睡覺,每週都要強迫自己坐出租車去新加坡機場,單程要花 2-3 個小時。即使我想和家人在一起,也很難。” ——我完全可以想象我爸爸有多累,尤其是工作要求他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大。
與此同時,我媽媽也竭盡全力撫養我們。她不僅盡心盡力照顧我妹妹的病情,還盡其所能地照顧我們(直到現在我才明白這一點)。她開車帶我們到新加坡各地參加數學和中文課後補習班。她每週兩次開車去義順送我去上高爾夫課。不僅如此,她還從事房地產經紀人的工作,讓那些想在新加坡購買房產的印尼家庭認識她,當時新加坡是一個流動性強、利潤豐厚的市場。
儘管兩個人都很堅強,我媽媽和爸爸的關係還是慢慢開始破裂。也許是因為不合拍。也許是因為距離。但作為一個孩子,雖然還小,我卻能觀察到他們的關係正在慢慢地逐漸消亡。一週又一週。
家裡吵架越來越頻繁。隨著時間流逝,每次吵架都變得越來越激烈。不僅我爸媽之間開始吵架,而且憤怒逐漸影響到整個家庭。我記得上中學的時候,我問過教會的導師: “我爸媽會離婚嗎?”事情似乎隨時都有可能崩盤。我能感覺到,我爸媽都非常不開心。
由於家庭生活不和諧,我退縮到自己的世界中。那是在我 11-14 歲的時候。說實話,無法與他人分享這些經歷是很難的(尤其是在那個年齡)。我沉迷於電子遊戲,信心低落。除此之外,我還患有嚴重的囊腫性痤瘡,這看起來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實際上卻加劇了我的病情,讓我的信心不斷下降,尤其是在中學時期,那時孩子們最頑劣,而我最自卑。
至少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在哪方面天賦異稟。我的學業成績可能高於平均水平,但我並不是第一名。我在體育、音樂等幾乎所有方面都不是特別優秀。這也打擊了我的自信心。
我記得在我 11 到 14 歲之間的時候,我曾陷入嚴重的抑鬱症。
這一切最終導致我父母在我 18 歲時離婚。說實話,當時的情況非常混亂。雙方關係不好,離婚的後果很難處理。然而,如果說這件事有什麼好處的話:那就是它鍛鍊了我長期忍受痛苦的能力,迫使我獨立並找到自己的道路。
我很幸運,從這件事中我與我媽媽和爸爸的關係都得到了改善。我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我決定回到印度尼西亞解決這個問題,稍後我會談到),也謙虛了自己,才走到今天這一步,可以說我不再怨恨。作為一家金融服務公司的創始人,我很享受現在能夠與我爸爸建立的聯繫和指導(邊喝葡萄酒邊談)。我也享受著與媽媽更好的關係和無比的感激,她為養育我和妹妹犧牲了自己,付出了很多。
高中:我的“激情”與長跑的誕生
我痴迷於努力工作。“當天才不努力時,努力工作會戰勝天才”。“冠軍是在休賽期誕生的”。這些都是我常說的格言。
但值得注意的是,成為一名運動員並不是我人生這一階段最難忘的部分。我發現自己被創造行為和創造超越自我的影響所吸引。
建立 Eagles Distance 項目讓我意識到,我可以參與創建一些對他人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項目。我可以利用我獲得的知識和能力對他人產生積極影響。從很多方面來說,這是我後來培養的創業精神的火花。
我在高中的表現非常出色。學術和課外活動的優秀為我打開了一扇大門,我選擇去西北大學攻讀數學本科學位。
西北大學:探索與展望
大學生活是我高中所學知識的自然延伸,特別是在創造力、創業精神、應對未知事物、獲得洞察力、領導力和勇氣等方面。
凱洛格與基石教育
決定移居印度尼西亞並在印度尼西亞旅行(COVID、貝恩、教育部)
其次,作為一個在“為美國而教”和 Cornerstone 工作期間將自己一生很大一部分時間奉獻給為他人提供教育機會的人,擴大教育機會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想要奉獻一生去建設的事情。
相反,回報會很多:我無疑會接觸到一個不同的環境,這個環境會推動我成長,與我的核心個人使命保持一致,而且我會與之前在印度尼西亞最大的科技公司擔任領導層的才華橫溢的印尼人一起磨練我的產品開發技能。
我深深內化並建立了自己的個人風險回報矩陣。引用摩根士丹利傳奇衍生品交易員和撲克專家亞倫·布朗在其非凡著作《華爾街的撲克臉》中談到在投資銀行招聘交易員時所說的話:
“我所傾聽的是,有人真正想要某種只有通過冒險才能獲得的東西,無論風險是大是小。
她是否巧妙地管理風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知道風險的存在,尊重風險,但還是接受了它。
大多數人一生都在漫無目的地徘徊,漫不經心地承擔著路上遇到的一切風險而得不到任何補償,卻從未有意識地承擔額外的風險來獲取金錢和身邊的其他好東西。
其他人則會本能地避免一切風險,或不加謹慎地抓住每一點閒錢。
我無意貶低這些策略;我相信這些策略對於追求它們的人來說是有意義的。只是我自己不理解它們。
我確實知道這些人中沒有一個人會成為成功的交易員。”
在教育部,我參與了超過 100 人的產品組織中的兩個主要團隊:產品戰略團隊和教育者平臺團隊。實際上,我負責在整個組織內建立產品的集體最佳實踐,幫助制定教育重點領域(恰好是 K-12 教育者垂直領域)的核心產品戰略,並在以內容共享和策劃為中心的垂直領域領導我自己的產品(想象一個小眾 YouTube,但內容專門用於教育者分享如何教學),在一個已有 300 多萬註冊教師的平臺上。
技能組合構建是方程式的一部分。與貝恩類似,我在 GovTech 磨練了我的核心產品技能。從戰術發現研究和通過機會樹確定優先級,運行 Google Ventures 的靈感設計衝刺、UX 映射、實驗設計和多變量測試、機器學習設計、GTM/發佈準備,當然還有編寫大量 PRD、說服大量工程師和設計師執行給定的計劃,並將進展傳達給領導層——我很快就學會了如何成為一名熟練的產品經理。網上有很多可用的資源,從書籍到 Reforge/Maven,這很有幫助。我學到的東西證實了我在貝恩不會開發很多重要的技能組合構建,因此證實了我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深入印尼是我經歷的另一個核心部分。為了克服我缺乏的印尼語能力,我每週上 4-5 次語言課,每次 2 小時。我記得我的老師取笑我,說我是她教的第一個印尼人。我強迫自己學習商業內容,從頭到尾聽 Gita Wirjawan 的《Endgame》,確保翻譯和理解他們對話的每一部分。這些內容還產生了額外的副作用,讓我對印尼創業生態系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慢慢地,我的印尼語水平越來越好。至少我可以讓自己理解一點。
最難忘的經歷是參加與部內領導的會議,並召開戰略規劃會議以最終確定我們的路線圖。我與領導們打破僵局,為我的蹩腳印尼語道歉(“Ibu/Bapak,mohon maaf Bahasa Indonesia saya tidak lancar”)。我開玩笑地告訴他們我每週上 5 節課,他們都很高興,開玩笑地回擊說我現在必須免費教他們英語。我特別清楚地記得這些課程,因為我最初的一個大恐懼已經消除了。
我意識到,這個問題是我需要參與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即將完成在教育部為期一年的計劃任務,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我下半輩子要解決什麼問題。
並且,偶然地,我意識到,正如上帝經常做的那樣,一旦你專心做某事:把機會擺在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