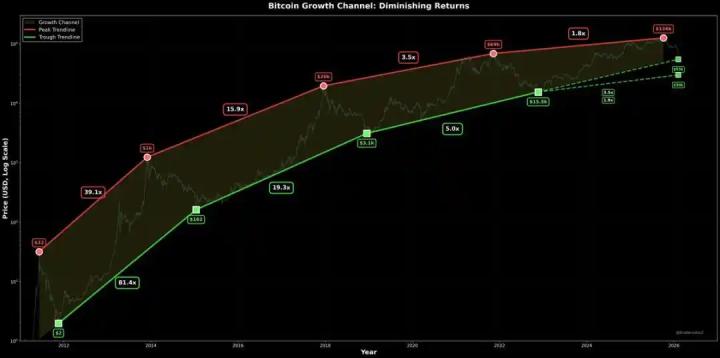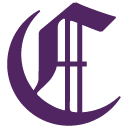作者:Prathik Desai,來源:TokenDispatch,編譯:Shaw 金色財經
20世紀80年代末,內森·莫斯特(Nathan Most)在美國證券交易所工作。不過,他既不是銀行家,也不是交易員。他是一物理學家,在物流行業工作多年,從事金屬和大宗商品的運輸。金融工具並非他的起點,實用系統才是。
當時,共同基金是獲得廣泛市場敞口的熱門方式。它們為投資者提供了多元化投資,但存在延遲。你無法全天候交易。你下單後,要等到市場收盤才能知道成交價格(順便說一下,它們至今仍是這種交易方式)。這種體驗感覺過時了,尤其是對於那些習慣了實時買賣個股的人來說。
內森提出了一個變通方案:開發一種追蹤標準普爾 500 指數但交易方式類似單股的產品。將整個指數打包成一種新的形式,在交易所上市。這一提議遭到了質疑。共同基金的設計初衷並非像股票那樣買賣。相關的法律框架當時並不存在,而且市場似乎也沒有這方面的需求。
但他還是繼續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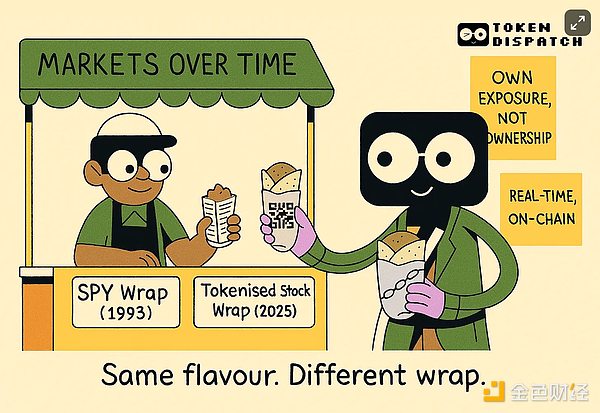 1993年,標準普爾存託憑證(SPDR)以股票代碼SPY首次亮相。它本質上是首個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一種代表數百種資產的工具。最初,它被視為一種小眾產品,後來逐漸成為全球交易最活躍的證券之一。在許多交易日,SPDR的交易量甚至超過了其追蹤的股票。SPY的合成結構比其標的資產獲得了更高的流動性。
1993年,標準普爾存託憑證(SPDR)以股票代碼SPY首次亮相。它本質上是首個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一種代表數百種資產的工具。最初,它被視為一種小眾產品,後來逐漸成為全球交易最活躍的證券之一。在許多交易日,SPDR的交易量甚至超過了其追蹤的股票。SPY的合成結構比其標的資產獲得了更高的流動性。
如今,這個故事再次顯得意義非凡。並非因為又有新基金推出,而是因為鏈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Robinhood 、Backed Finance 、Dinari和 Republic 等投資平臺開始提供代幣化股票——基於區塊鏈的資產,旨在反映特斯拉、英偉達等上市公司甚至 是像OpenAI這樣的私營公司的價格。
這些代幣的定位是獲取曝光度,而非所有權。這些代幣被宣傳為一種獲得曝光度的方式,而非所有權。它們不具備股東身份,也沒有投票權。你購買的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股權。你持有的是與股權相關的代幣。
這種區別很重要,因為圍繞這一點已經存在爭議。
OpenAI 甚至埃隆·馬斯克都對 Robinhood 提供的代幣化股票表示擔憂。
 隨後,Robinhood 首席執行官 Tenev不得不澄清,這些代幣實際上讓散戶投資者能夠接觸到這些私人資產。
隨後,Robinhood 首席執行官 Tenev不得不澄清,這些代幣實際上讓散戶投資者能夠接觸到這些私人資產。
與公司自行發行的傳統股票不同,這些股票是由第三方創建的。有些聲稱持有真正的股票並進行託管,提供 1:1 的支持,而有些則是完全合成的。這種體驗讓人感覺很熟悉:價格像股票一樣波動,界面類似於經紀商應用程序,儘管其背後的法律和金融實質往往更薄弱。
不過,它們仍然吸引著特定類型的投資者。尤其是那些美國以外的投資者,他們無法直接投資美國股票。如果你住在拉各斯、馬尼拉或孟買,想要投資英偉達,通常需要開設外國經紀賬戶,滿足較高的最低餘額要求,並且要經歷漫長的結算週期。而一種在鏈上交易並追蹤標的股票在交易所走勢的代幣省去了交易過程中的摩擦。想想看,沒有電線,沒有表格,沒有門檻,只需一個錢包和一個市場。
這種訪問方式感覺很新穎,儘管其機制與舊有的類似。
但這裡存在一個實際問題。許多此類平臺——Robinhood、Kraken 和 Dinari——並未在美國以外的許多新興經濟體運營。例如,目前尚不清楚印度用戶是否能夠通過這些途徑合法且實際地購買代幣化股票。
如果代幣化股票要真正拓寬進入全球市場的渠道,面臨的阻礙將不只是技術層面的,還會有監管、地域和基礎設施方面的。
衍生品的運作方式
期貨合約長期以來一直提供一種無需觸及標的資產即可進行預期交易的方式。期權則允許投資者表達對波動性、時機或方向的看法,通常無需購買股票本身。在每種情況下,衍生品都成為投資標的資產的另一種途徑。
代幣化股票也帶著類似的目的出現。它們並不宣稱比股票市場更優越。它們只是提供了另一種進入方式,尤其是對於那些長期以來一直被排除在公共投資之外的人來說。
新的衍生產品通常會遵循一個可識別的發展軌跡。
起初,市場一片混亂。投資者不知如何定價,交易員對風險猶豫不決,監管機構也退縮不前。隨後,投機者蜂擁而至。他們試探底線,拓展產品,利用其中的不均衡獲利。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產品被證明有效,就會被更多主流參與者採用。最終,它成為基礎設施。
指數期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和幣安(Binance)上的比特幣衍生品,最初的情況都是如此。它們最初並非是面向所有人的工具。起初這些是投機的遊樂場:速度更快,風險更高,但更靈活。
代幣化股票也可能遵循同樣的發展路徑。起初,散戶投資者會使用它們來獲取難以觸及的資產(如 OpenAI 或未上市公司的)敞口。隨後,套利者會利用代幣與基礎股票之間的價格差進行操作。如果交易量保持穩定且基礎設施逐漸成熟,機構交易部門也可能會開始使用它們,尤其是在合規框架逐漸完善的司法管轄區。
早期市場交易活動可能看起來很嘈雜,流動性稀薄,價差較大,週末還會有價格缺口。但衍生品市場往往就是這樣起步的。它們絕非完美複製品。它們是壓力測試,是市場在資產本身調整之前發現需求的方式。
這個結構結構具有有趣的特性或缺陷,這取決於人們如何看待它。
傳統股票市場有開盤和收盤時間。即使大多數基於股票的衍生品交易也僅在市場交易時間內進行。但代幣化的股票並非總是遵循這種節奏。如果一隻美國股票在週五收盤價為 130 美元,而週六發生了重大事件——比如收益洩露或地緣政治事件——代幣可能會開始波動,即便股票本身處於靜止狀態。
這使得投資者和交易員能夠在股市休市期間將陸續傳來的消息納入考量。
只有在代幣化股票的交易量顯著大於普通股票交易量的情況下,時間差才會成為一個問題。
期貨市場通過資金費率和保證金調整來應對這類挑戰。交易所交易基金依靠授權參與者和套利機制來維持價格穩定。至少到目前為止,代幣化股票還沒有這些系統。價格可能會偏離,流動性可能不足。而且代幣與其參考資產之間的聯繫仍然依賴於對發行方的信任。
然而,這種信任程度各不相同。當 Robinhood 在歐盟發行 OpenAI 和 SpaceX 的代幣化股票時,兩家公司均否認參與其中。雙方既沒有協調,也沒有正式的合作關係。
這並不是說代幣化股票發行本身存在問題。但值得思考的是,在這些情況下你到底在買什麼。是價格敞口,還是一種權利和追索權都不明確的合成衍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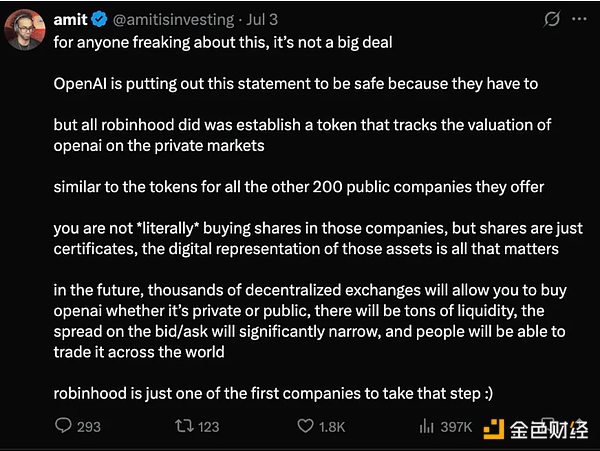 這些產品的底層基礎設施也大相徑庭。有些是依據歐洲框架發行的。有些則依賴智能合約和離岸託管人。還有少數平臺,比如 Dinari,正在嘗試更受監管的方式。大多數仍在試探法律允許的極限。
這些產品的底層基礎設施也大相徑庭。有些是依據歐洲框架發行的。有些則依賴智能合約和離岸託管人。還有少數平臺,比如 Dinari,正在嘗試更受監管的方式。大多數仍在試探法律允許的極限。
在美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已已表明了其對代幣銷售和數字資產的態度,但傳統股票的代幣化形式仍處於灰色地帶。平臺也持謹慎態度。例如,Robinhood 的發行地點是歐盟,而不是其本土市場。
即便如此,需求仍然顯而易見。
Republic 為 SpaceX 等私營公司提供了合成通道。Backed Finance 將公開發行的股票打包並在 Solana 上發行。這些嘗試尚處於起步階段,但卻在持續進行,並且背後有一個旨在解決摩擦而非金融問題的模式。代幣化股票發行可能無法改善所有權的經濟狀況,因為這不是他們想要實現的目標。他們只是想簡化參與體驗。或許吧。
對於散戶投資者來說,參與度往往是最重要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代幣化股票並非與股票競爭,而是與獲取股票所需付出的努力競爭。如果投資者只需輕點幾下,通過一個也持有其穩定幣的應用程序就能獲得英偉達的定向敞口,他們可能就不會在意該產品是合成的。
不過,這種偏好並非新鮮事。SPY 的研究表明,包裝產品可以成為主要市場。差價合約、期貨、期權和其他衍生品也是如此,它們最初是交易員的工具,但最終服務於更廣泛的受眾。
這些衍生品往往甚至領先於標的資產。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它們比其下方的較慢市場更快地吸收了市場情緒,反映出恐懼或貪婪。
代幣化股票可能會遵循類似的路徑。
基礎設施尚處於起步階段,流動性不均衡,監管缺乏透明度。但潛在的推動力是顯而易見的:打造一種能反映資產、更易於獲取且足以吸引人們參與的事物。如果這種表徵能保持其形態,就會有更多資金通過它流動。最終,它不再是影子,而是信號。
內森·莫斯特 (Nathan Most) 的初衷並非重新定義股票市場。他看到了低效之處,並尋求更流暢的界面。如今的代幣發行者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只不過這一次,充當包裝的是智能合約,而非基金結構。
有趣的是,這些新包裝能否贏得信任,尤其是在市場動盪時,這一點值得觀察。
它們並非股權,也不是受監管的產品。它們是便捷的工具。對於許多用戶而言,尤其是那些遠離傳統金融或身處偏遠地區的人來說,這種便捷性可能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