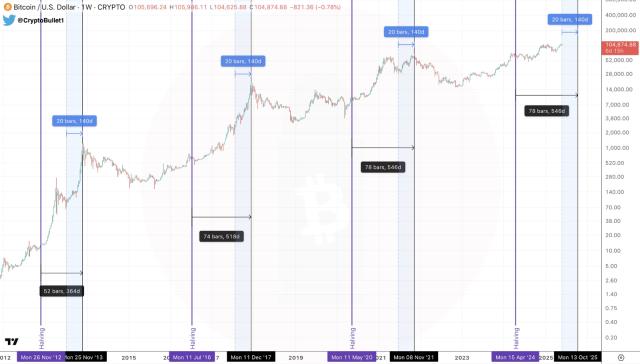來源:The Atlantic
作者:Josh Tyrangiel
原標題:America Isn’t Ready for What AI Will Do to Jobs
編譯及整理:BitpushNews
全文約 2.5 萬字,閱讀大約需 45 分鐘
1869年,馬薩諸塞州的一群改革者說服州政府嘗試一個簡單的想法:計數。
當時,第二次工業革命正轟鳴著席捲新英格蘭地區。它給工廠主們上了一課——如今大多數MBA學生在第一學期就會學到這一課:效率的提升往往是有代價的,而這個代價通常由別人承擔。那些新式機器不僅是在紡棉花或鍛造鋼鐵,它們的運轉速度超出了人類軀體的承受極限——要知道,人體這件精密的工程作品經過數百萬年的演化,原本是為完全不同的目的而設計的。工廠主們深知這一點,正如他們也知道,人類對苦難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一旦超過底線,他們就會開始放火燒東西。
儘管如此,機器依然在全速推進。
因此,馬薩諸塞州成立了全美第一個“勞工統計局”,希望數據能完成良知無法完成的任務。
政策制定者認為,通過衡量工作時長、環境、工資,以及經濟學家現在稱之為“負外部性”、而當時被稱為“被扯掉的孩子手臂”的數據,他們或許能為所有人創造一個相對公平的結果。或者,如果你更憤世嫉俗一點,那叫作“可持續的剝削水平”。
幾年後,隨著聯邦軍隊向罷工的鐵路工人開火,而富裕公民紛紛資助私人軍火庫——這些跡象表明社會運行得並不順利——國會認為這個主意值得大規模推廣,於是成立了聯邦勞工統計局(BLS)。
統計並不能廢除不公,甚至很少能平息爭論。但這種“計數”的行為——試圖看清事實,並承諾政府將遵循一套共享的事實——信號了一種追求公平的意願,或者至少表現出正在為此努力。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意願至關重要。這是一個共和國贏得信任的方式之一。
BLS 堪稱文明的一個小奇蹟。它每個月向約 60,000 個家庭、120,000 家企業和政府機構發送詳細調查,並輔以定性研究來核實和修正發現。它確實為美國社會這份“成績單”貢獻了一份力量:整整 250 年,美國沒有發生暴力階級戰爭。此外,你不得不佩服其細枝末節數據中的娛樂價值。
正是通過 BLS,我們才知道:2024 年,有 44,119 人從事移動餐飲服務(即餐車),比 2000 年增長了 907%;非獸醫寵物護理(美容、訓練)僱傭了 190,984 人,增長了 513%;美國擁有近 10 萬名按摩治療師,而在加州napa市,這一職業的集中度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五倍。
這些以及數以千計的其他 BLS 統計數據描繪了一個日益繁榮的社會,以及一個能永遠適應變化的勞動力群體。但與所有統計機構一樣,BLS 有其侷限性。它極擅長揭示已經發生的事,但在告訴我們即將發生什麼方面,作用非常有限。數據無法預見經濟衰退或全球疫情——也無法預見某種可能像隕石撞擊恐龍一樣衝擊勞動力市場的技術的到來。
CEO們的陽謀
我指的當然是人工智能(AI)。
在經歷了一場本可以由 H.P. 洛夫克拉夫特導演的亮相後——埃隆·馬斯克曾在早期發出典型的警告:“我們正在召喚惡魔”——AI 行業已經從噩夢般的語言轉向了令人昏昏欲睡的企業術語:驅動創新、加速轉型、重構工作流。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人類發明了某種真正奇蹟般的東西,卻急於給它套上一件普通的企業抓絨背心。
向企業銷售軟件確實可以賺得盆滿缽滿,但淡化 AI 的衝擊力也是一種有用的偽裝。這項技術可以在你喝完咖啡前消化掉一百份報告,起草和分析文件的速度比整個法律助手團隊還快,創作出的音樂與流行歌星或朱利亞德學院畢業生的天才之作難分伯仲,還能編程——是真正的編程,而不只是從 Stack Overflow 上覆制粘貼——且精準度堪比頂尖工程師。那些曾經需要技能、判斷力和多年培訓的任務,現在正由能夠不斷自我學習的軟件冷酷無情且持續不斷地執行著。
AI 已經無處不在,任何聰明的知識工作者都可以將工作中的繁瑣部分交給機器處理。包括微軟和普華永道在內的許多公司已經指示員工利用 AI 來提高效率。
但任何將任務分包給 AI 的人都足夠聰明,能夠想象接下來的場景:總有一天,“增強”會演變成“自動化”,認知層面的過時會迫使他們去餐車、寵物水療中心或按摩店尋找工作。至少在人形機器人到來之前是這樣。

許多經濟學家堅持認為一切都會好起來。
資本主義是有韌性的。ATM 機的普及反而讓銀行櫃員的僱傭量增加了,Excel 的引入增加了會計人數,Photoshop 的出現刺激了對平面設計師的需求。在每一個案例中,新技術都自動化了舊任務,提高了生產力,並創造了比以往任何人能想象的薪水更高的職位。
BLS 預測,未來 10 年就業將增長 3.1%。這雖然低於前十年的 13%,但在人口穩定的國家,增加 500 萬個新工作崗位算不上災難。
然而,有些東西是經濟學家難以衡量的。美國人傾向於從他們所做的工作中獲得意義感和身份認同。大多數人不想改行,即便他們有信心能找到別的工作——而事實上他們並沒有這種信心。2025 年 8 月路透社/益普索的一項民調顯示,71% 的受訪者擔心人工智能會“導致太多人永久失業”。
若非現代“工廠主”們早已公開預言AI將“永久消滅崗位”,這份顯示公眾恐慌的數據,或許只會被當作又一次杞人憂天。
2025 年 5 月,AI 公司 Anthropic 的 CEO 達里奧·阿莫迪表示,AI 可能會在未來一到五年內將失業率推高 10% 到 20%,並“抹除一半的初級白領工作”。福特汽車 CEO 吉姆·法利估計,十年內它將裁掉“整整一半的白領員工”。
OpenAI 的 CEO 山姆·奧特曼透露,他與科技圈 CEO 朋友的小群裡甚至有一個賭局:賭哪一天會出現一家只有一名員工的估值十億美元的公司(本雜誌的業務部門與 OpenAI 建立了合作伙伴關係)。
其他公司,包括 Meta、亞馬遜、聯合健康、沃爾瑪、摩根大通和 UPS,最近都宣佈了裁員,並在給投資者的報告中用了更委婉的說法,如“自動化”興起和“員工總數呈下降趨勢”。
綜合來看,這些聲明極其反常:資本家們警告工人他們腳下的冰即將破裂——同時繼續在上面跺腳。
這就像我們在觀看同一個場景的兩個版本。在版本一中,冰層穩如泰山,因為它向來如此;在版本二中,許多人沉入水底。區別只有在表面最終塌陷的那一刻才會清晰——而到那時,可供選擇的方案將變得極其有限。
AI 已經在通過一個接一個被委派的任務來改變工作。如果轉型足夠緩慢,經濟調整足夠迅速,經濟學家可能是對的:我們會沒事的。甚至會更好。但如果 AI 觸發的是一場快速的勞動力重組——將數年的變化壓縮到數月內,並影響全球約 40% 的職位(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預測的那樣)——其後果將不僅止於經濟層面。它們將考驗那些已經顯現出脆弱性的政治機構。
那麼,問題在於我們正接近的這場劇變,是可以用統計手段管理的,還是那種殘忍到讓人不忍統計的那種?
後視鏡:經濟學家的盲點
奧斯坦·古爾斯比是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教授,曾任奧巴馬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他也是少數幾個讓你在聚會上碰到也不會覺得無聊的經濟學家。
當我問古爾斯比是否有確鑿數據表明 AI 已開始侵蝕勞動力市場時,他給出了一個既顯而易見又毫無幫助的回答,且帶著微笑。他答了,似乎又沒答。
我認識古爾斯比很久了,很享受這種時刻——他會自嘲我們作為專業人士的無力感。經濟學家很少能對當下給出直接答案,而記者則討厭未來不在截止日期前揭曉。
我們在 9 月進行了交談,當時被稱為“金絲雀論文”的研究報告剛剛發佈。斯坦福大學數字經濟實驗室的三位學者通過分析數百萬份受生成式 AI 影響的職位薪酬記錄得出結論:22 至 25 歲的工人——即“金絲雀”——自 2022 年底以來,就業率下降了約 13%。
連續幾天,這份報告是該領域所有人都想談論的話題,而談論主要指挑毛病。
有人說報告過分誇大了 ChatGPT 的影響;有人說年輕人就業本就具有周期性;還有人指出同一時期利率大幅飆升才是更可能的波動源。此外,“金絲雀”報告也與經濟創新中心幾周前發佈的一項研究相矛盾,後者認為 AI 短期內不太可能導致大規模失業,儘管它會重塑工作和工資。那篇研究的標題極具挑釁性:“AI 與就業:定論(在下一個結論出現前)”。
這就是古爾斯比想要強調的:經濟學家受數字約束。而從數字上看,沒有任何跡象表明 AI 已經影響了人們的工作。“現在下結論還太早,”他說。
缺乏確定性不應被誤認為是缺乏擔憂。美聯儲的職責是促進最大化就業,因此企業關於即將裁員的聲明引起了古爾斯比的關注。但數據對不上。
有一種可能是勞動力市場比看起來更疲軟,但這種疲軟被企業內部消化了,而沒有體現在失業率上。然而,如果公司囤積了超過需求的工人(即“勞動力囤積”現象),你應該會看到生產力增長疲軟。這就像宿醉一樣可以預見:工人太多,活兒不夠,生產力下降。“但事實恰恰相反,”古爾斯比說,“生產力增長一直非常高。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這一點。”
生產率是通往更繁榮社會的捷徑。如果每個工人在相同時間內能生產更多——更多商品,更好服務,更快結果——那麼即使工人數量不增加,經濟總量也會增長。這是罕見的生產率提升,能擴大整體經濟蛋糕,而不僅僅是重新分配份額。
過去幾年,美國的生產力一直處於爆發期。這可能是暫時的,是由於某種一次性提振導致的,比如疫情催生的小微企業創業潮。但古爾斯比帶著那種以把簡單問題複雜化為樂的態度指出,像電力和計算機這樣的通用技術可以創造持久的生產力提升,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富裕。
AI 是否屬於這類技術,只有時間能給出答案。需要多久?“數年時間,”古爾斯比說。
與此同時,還有另一個變數。就業面臨的直接風險可能不是 AI 本身,而是企業被 AI 的前景所誘惑,在還沒搞清楚它到底能做什麼之前就過度投資。古爾斯比回想起互聯網泡沫時期,當時公司瘋狂投資鋪設光纖和建設產能。“2001 年,當我們發現互聯網的增長率不是每年 25%,而僅僅是 10% 時——儘管這依然是很棒的增速——這意味著我們的光纖太多了,隨後便發生了商業投資崩盤。一大批人以‘傳統的方式’丟掉了工作。”
如果 AI 投資也發生類似的崩潰,情景可能會非常熟悉:痛苦、不穩定,並伴隨著媒體的謾罵與指責。但這只是財務上的重置,而非技術上的倒退——這是經濟學家最擅長識別的結果,因為它以前發生過。
這就是經濟學的悖論。為了理解當下將我們推向未來的速度有多快,你需要一個固定參照點,而所有的固定點都留在過去。這就像只看著後視鏡開車——如果路是直的,這很有挑戰;如果路不是直的,那就是災難性的。
大衛·奧托爾和達隆·阿西莫格魯是這一領域最優秀的“後視鏡駕駛員”。兩人都在麻省理工學院,都擅長理解之前的經濟動盪。阿西莫格魯是 202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研究不平等;奧托爾則專注於勞動力。兩人都堅持認為,AI 及其後果的故事將主要取決於“速度”——不是因為他們假設失去的工作會自動被取代,而是因為較慢的變革速度能給社會留出適應的時間,即便其中一些工作永遠消失。
勞動力市場有其自然的調節率。如果在 30 年的時間裡,某個職業每年有 3% 的員工退休或被裁減,你幾乎感覺不到。但十年後,該職業三分之一的工作就消失了。電梯操作員和收費站管理員就經歷過這種緩慢的淡出,並沒有對經濟造成損害。“當變化發生得更加迅速時,”奧托爾告訴我,“事情就會變得很麻煩。”
奧托爾最著名的工作是關於“中國衝擊”的研究。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六年後,美國13%的製造業崗位——約200萬個——消失了。“中國衝擊”對小型製造業——紡織、玩具、傢俱——造成了不成比例的打擊,主要集中在南部。“許多地方的工人至今仍未恢復,”奧托說,“而我們顯然正在承受政治後果。”
但 AI 不是貿易政策,它是軟件。即使它最先衝擊某些職業和地區——比如大型城市律所的律師可能比數字化程度較低行業的工人早幾年感受到衝擊——這項技術也不會受地理限制。最終,每個人都會受到影響。
這一切聽起來很不祥,直到你記住關於軟件最重要的一點:人們討厭它,幾乎就像討厭變化一樣。
這就是讓許多經濟學家相信 AI “隕石”至少還有十年路程的原因。
“那些科技公司 CEO 們希望我們相信,自動化市場是命中註定的,一切都會順利且有利可圖地發生,”阿西莫格魯說。接著,他發出一聲諾獎級別的嗤之以鼻,“歷史告訴我們,它實際上會發生得慢得多。”
論據如下:
在 AI 能夠改變一家公司之前,它必須接入公司的內部數據並編織進現有系統中——這聽起來容易,前提是你不是首席技術官(CTO)。大多數財富 500 強公司的一個行業秘密是:它們仍有許多關鍵功能運行在沉重、工業級的“大型機”計算機上。這些機器幾乎從不出故障,因此也永遠無法被替換。大型機就像克里斯托弗·沃肯:它們從 1960 年代就開始馬不停蹄地工作,在執行特定角色(處理支付、保障數據)方面表現卓越,而且現在幾乎沒人真正理解它們的工作原理。
將遺留技術與現代人工智能集成,意味著要協調硬件、供應商、合同、古老的編程語言和人——其中每一個人對“正確”的變革方式都有強烈的看法。幾個月過去了,然後幾年過去了;公司派對來了又去;首席執行官仍然無法理解為什麼人工智能的奇蹟沒有解決他們所有的問題。
每一種新的通用技術在一段時間內都會被舊事物的混亂“劫持”。第一批發電站早在 1880 年代就開業了,當時沒人爭論電力是否優於蒸汽機。但由於工廠是圍繞地下室的蒸汽機建造的,動力通過貫穿建築的長軸、皮帶和滑輪傳輸到各臺機器。為了採用電力,工廠主不只是需要買個電機,他們需要推倒並重建整個工廠。有些確實這麼做了,但大多數只是等待現有設施磨損報廢,這解釋了為什麼電力帶來的重大經濟收益在 40 年後才顯現出來。
然而,這些解釋對於經濟學家安東·科裡內克來說並不足以令人寬慰。他告訴我很“超級擔心”。他認為美國最早在今年就會看到重大的失業情況——“一個非常明顯的勞動力市場效應”。
“然後你交談過的那些經濟學家會說:‘我從數據裡看到了!’”科裡內克停頓了一下,“我們別開玩笑了,因為這太嚴肅了。”
科裡內克是弗吉尼亞大學教授,也是“變革性 AI 經濟學倡議”的教席主任。去年,《時代》週刊將其列入 AI 領域最具影響力人物名單。但他最初並不想成為經濟學家。他在奧地利的一個山村長大,用0和1編寫機器代碼——最不迷人的編程形式,也是最嚴苛的。它教會你指令在哪裡形成瓶頸,系統在哪裡堵塞,以及壓力過大時什麼會首先崩潰。
自 2010 年代初深度學習取得突破以來,他一直密切關注 AI 的發展,儘管他的博士論文關注的是金融危機預防。當他在 2022 年 9 月第一次看到大語言模型的演示時,只用了“大約五秒鐘”就開始思考它對未來工作的影響,首先從他自己的工作開始。
我們在秋天的夏洛茨維爾共進早餐。科裡內克年輕苗條,戴著精緻的細框眼鏡,留著淺紅色鬍鬚。給我的整體印象是:他寧願去自定義 Excel 選項卡,也不願預言末日。然而,他在這裡說出了經濟學家最鄙視的五個字:這次可能不一樣。

科裡內克論點的核心很簡單:他的同事們沒有讀錯數據,但他們讀錯了技術。“我們無法完全構想出擁有‘非常聰明’的機器意味著什麼,”科裡內克說,“機器一直以來都是笨的,所以我們不信任它們,推廣它們總需要時間。但如果它們比我們更聰明,在很多方面它們可以‘自我推廣’。”
這已經發生了。體育賽事期間,許多讓人看不懂的廣告都在推銷 AI 工具,這些工具承諾能加速其他 AI 工具進入大公司工作流的速度。由於其中許多系統不需要大規模新硬件或人工重寫系統,部署時間縮短了多達 50%。
這就是科裡內克與“後視鏡”經濟學家分道揚鑣的地方。如果 AI 的移動速度如他預期的那樣快,對許多工人來說,傷害將在機構能夠適應之前就到達——而每一次成功的應用只會增加更多應用的壓力。
以諮詢公司為例,它們一直通過初級助理做研究和起草報告來收取高昂費用。客戶之所以容忍這些費用,是因為沒有替代方案。但如果一家公司能利用 AI 以更快、更低廉的價格交付同樣的成果,其競爭對手就面臨殘酷的選擇:要麼採用該技術,要麼解釋為什麼他們還要為人力工時收取溢價。一旦有一家公司接入 AI 並削弱對手,其餘公司要麼迅速跟進,要麼被淘汰。競爭不僅獎勵採用者,還讓延遲採用變得無法原諒。
科裡內克承認那兩個標準的反對意見:數據目前還不明確,且新技術歷史上創造的就業多於摧毀的。但他認為,他的同行們需要開始盯著前方開車。“每當我與西海岸實驗室的人交談時”——科裡內克是 Anthropic 經濟顧問委員會的無薪成員——“我並不覺得他們是在人為地誇大產品的潛力。我通常感覺到,他們和我一樣恐懼。我們至少應該考慮一種可能性:他們告訴我們的「可能」真的會「成真」。”
科裡內克不確定技術本身是否可以通過政策來引導,但他希望更多經濟學家進行情景規劃,以免政策制定者措手不及。因為大規模失業不只是失業,它還意味著貸款逾期、級聯式違約、消費需求萎縮,以及一種自我強化的衰退——這種衰退能將衝擊轉變為危機,將危機轉變為帝國的衰落。
在 2025 年初那段短暫的時期,CEO 們還興致勃勃地提供關於 AI 及其對員工和利潤影響的“思想領導力”。但隨後,這些表態幾乎在同一時間詭異地停止了。任何見過鯊魚鰭劃破水面然後消失的人都知道這並不能讓人安心。
勞工統計局給出了一個簡單的解釋:美國僱傭了約 280,590 名公共關係專家,過去二十年增長了 69%(人數幾乎是記者的 7 倍)。不難想象他們的專業建議:AI 不受大眾歡迎,談論裁員的 CEO 更不受歡迎。所以,關於 AI 和工作的話題,乾脆閉嘴吧?
10 月,在《紐約時報》披露亞馬遜高管計劃到 2033 年可能自動化超過 60 萬個職位的第二天,一家大型跨國公司的 PR 主管告訴我:“我們絕對不再談論這個話題了。”這至少創造了一點小小的歷史——這是第一次有人要求我允許其匿名,以便在記錄中解釋他們將不再對外發聲。
也就是說,沃爾瑪、亞馬遜、福特等財富 100 強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以及 Anthropic、Stripe 和 Waymo 等新興 AI 驅動公司的高管——這些在幾個月前還對 AI 和就業滔滔不絕的人——要麼拒絕、要麼忽略了本報道的多次採訪請求。甚至連商業圓桌會議——一個由美國 200 家最強大公司的 CEO 組成的協會,本就是為了代表成員就此類問題發聲而存在的——也告訴我其首席執行官、前小布什政府白宮幕僚長約書亞·博爾滕“無話可說”。
當然,告訴記者不發表公開評論並不等於真的閉嘴。這些 CEO 至少在和一個人交談:LinkedIn 聯合創始人、微軟董事會成員裡德·霍夫曼。霍夫曼從出身看是技術專家,從性情看是樂觀主義者。他認識企業界的每一個人,每個人也都知道他認識每一個人,這使他成為硅谷最受歡迎的“明白人”——一個理性、中立的傳聲筒,CEO 們想大聲思考時可以去找他。
他告訴我,AI 已經將 CEO 們分成了三類。
第一類是涉獵者:這些遲到者終於開始花點高質量的時間和他們的首席技術官(CTO)待在一起。
第二類則出於虛榮心,或者渴望讓他們那些傳統的業務被技術達人們更認真地對待,於是急於宣佈自己是 AI 領袖。“他們就像在說:‘看我!我很重要!我處於核心地位。’但實際上他們還沒做任何實事,”霍夫曼說,“他們只是想:‘也給我安排一個 AI 牌桌上的位置。’”
第三類則截然不同:這些高管正在秘密制定轉型計劃。“他們是那些洞察先機的人。而且值得讚揚的是,我認為其中許多人都在思考如何通過教育、技能重塑或培訓,幫助整個員工隊伍完成轉型。”
但這三類人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相信——在聽了多年關於 AI 的承諾之後——投資者已經對“夢想”失去了耐心。今年,他們要看到結果。而 CEO 產生結果最快的方式就是裁員。霍夫曼說,裁員是不可避免的。“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說服自己,這件事只有一種結局。我認為這是想象力的匱乏。”
霍夫曼並不浪費時間去勸說 CEO 們不要裁員,他知道他們會裁。 “我告訴他們的是,你必須展示出除了削減成本之外,如何從 AI 中獲益的路徑和想法。你如何獲得更多收入?你如何幫助你的員工轉向更有效地使用 AI?”
「遲鈍」的華盛頓
“這是一場高燒,”曾任羅德島州州長、拜登政府商務部長的吉娜·雷蒙多告訴我說,她指的是那股裁員潮。“每個 CEO 和每個董事會都覺得他們需要快點、再快點。‘我們有 40,000 人做客戶服務?減到 10,000 人。剩下的交給 AI。’如果整件事的核心就是盯著效率快速移動,那麼會有非常多的人受到嚴重傷害。考慮到我們當下的情況,我認為這個國家承受不起這種衝擊。”
和霍夫曼一樣,雷蒙多佔據著一個獨特的生態位:她是一個走進董事會卻不會觸發對方“文化金屬探測器”警報的民主黨人。她曾聯合創立過一家風投公司,AI 公司的高管們認為她務實且精通技術,願意與她交談。“這是一項能讓我們更高效、更健康、更可持續的技術,”雷蒙多說,“但前提是我們必須非常認真地管理這一轉型過程。”
去年夏天,雷蒙多前往愛達荷州太陽谷參加了為期四天的艾倫公司會議(Allen & Co. conference),那裡被稱為“億萬富翁的夏令營”。她向人們提出了同樣的兩個問題:你如何使用 AI?當你這樣做時,你的員工會怎麼樣?
許多 CEO 承認他們感到左右為難。華爾街期望他們用 AI 取代人工;如果他們不這麼做,丟掉工作的就會是他們自己。但如果他們全都下令大規模裁員,他們知道後果將是巨大的——對他們的員工、對國家,甚至對他們作為人的良知。
雷蒙多的回應是:“這個國家最強大的 CEO 們有責任協助解決這個問題。”她預見了“大規模新型政企合作伙伴關係”的可能性。“想象一下,如果我們能讓公司承擔起對被裁人員進行重新培訓和重新安置的責任。”
她知道這聽起來像什麼。“很多人說:‘哦,吉娜,你太天真了。絕不可能發生。’好吧。但我告訴你們,如果我們不利用這個時刻換種方式做事,我們所熟知的美國就要終結了。”
如果這些高管的擔憂真如雷蒙多所想的那樣真誠,那麼也許他們可以被推動去採取行動。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主席利茲·舒勒正嘗試這樣做,但大多以失敗告終。她告訴我,CEO 和技術領袖們太專注於贏得 AI 競賽,以至於“勞動者成了一個被遺忘的附屬品”。
舒勒意識到,作為一名工會領袖,這種看法是意料之中的,於是她主動做出讓步:“大多數勞動者,尤其是工會領袖,最初都會感到恐慌,對吧?就像:‘哇,這基本會抹殺所有工作,所有人都會失去安全網,我們必須阻止它’——但我們知道這是不可能發生的。”舒勒說,她並沒有恐慌,而是與代表約 1,500 萬人的 AFL-CIO 各工會領袖交談,敦促他們在 AI 被強加給他們之前的短暫窗口期內,弄清楚他們想從這項技術中得到什麼,以及他們準備為此交換什麼。
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家公司接過了這根橄欖枝。微軟已同意讓員工參與有關開發 AI 及其治理準則的對話。 最引人注目的是,該協議包括一項“中立協議”,允許工人自由組建工會而不受報復——這在科技界是前所未有的。“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典範,”舒勒說,“我們希望看到其他人也承認,勞動者是這場辯論和我們未來的核心。”
眯起眼仔細看,你或許能說服自己,微軟的交易確實是一個“概念驗證”。但更有可能的是,這只是一個孤例。因為所有的勸誘、理性和對愛國主義及共同人性的呼籲,都在與一個和僱傭勞動歷史一樣古老的真理搏鬥:美國資本主義奔向效率的姿態,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不可避免、冷漠無情,且對任何恰好站在低處的人產生可預見的後果。 而有了 AI,資本第一次擁有了一個承諾實現近乎無限生產力的工具,這是當年的工廠主和磨坊主們做夢也不敢想的:以最少的員工索要利益分成,實現最大的效率。
在這種背景下,CEO 們的沉默帶上了一種不同的迴響。這可能是一種冷酷的承認,即決定已經做出;也可能是一種壓抑的懇求,希望政府能把他們從這種自我毀滅的競爭中拯救出來。
於是,視線轉回華盛頓。
你可能也意識到,我們現在的政治局面令人難以忍受。然而,讓它們變得可以忍受的唯一方法——找回其核心的一線希望——就是更多的政治博弈。這就是華爾街核心的笑話:正是那種讓這個地方變得空洞的掙扎,也是它獲得新生的唯一途徑。
如果有一個問題能夠緩解全美的“政治頭痛”——某種足夠龐大、足夠緊迫的問題——你可能會假設“美國就業的未來”就是那個問題。但密歇根州資深參議員加里·彼得斯告訴我說:“至少從我在參議院的接觸來看,沒多少人在談論它。”彼得斯(民主黨人)特別指出了共和黨人(儘管他也說雙方都有責任)的一種普遍心態:“就像在說:‘我們不需要做任何事。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事實上,政府就該靠邊站。讓行業繼續前進,繼續創新。’”

很難在不將美國科技霸權拱手讓給中國的情況下減緩人工智能發展——科技遊說團體帶著宗教般的狂熱強調這一點。要強迫 AI 實驗室提前通報其部署後果也很難,因為他們自己往往也搞不清楚。你可以監管替代工作的 AI 的使用,但執行需要一個目前尚不存在的監管機構,以及政府目前並不具備的技術專長。
話雖如此,政府在如何引導工人度過經濟衝擊方面擁有一套數十年的“劇本”。彼得斯一直在敲著桌子,試圖讓國會使用它。
自 1974 年美國開始更積極地向全球貿易開放經濟以來,“貿易調整援助”(TAA)計劃已幫助超過 500 萬人進行轉崗培訓、工資保險和搬遷補助,近年來每年的耗資約為 5 億美元。2018 年,彼得斯共同發起了《自動化 TAA 法案》,旨在將同樣的福利擴大到被 AI 和機器人擠壓的工人身上。它悄無聲息地夭折了,就像國會里的許多提案一樣。2022 年,TAA 的授權到期,而在一個對貿易投票和新增支出極度排斥的國會中,彼得斯恢復該計劃的努力一直毫無進展。
這非常愚蠢。美國目前有大約 700,000 個空缺的工廠和建築工作崗位。(諷刺的是,阻礙 AI 發展的少數因素之一,正是缺乏有資格在數據中心安裝冷卻系統的暖通空調(HVAC)技術人員。)預測半數白領工作可能消失的福特 CEO 吉姆·法利也一直在說,汽車行業短缺數十萬名能在經銷商處工作的技術人員——這些工作處於長期的“理想狀態”:技術含量足以賺取六位數的薪水,且依賴於精確的手工靈活性,難以被機器人化。但必須有人為這些崗位所需的數月培訓埋單。“這些是非常好的工作,”彼得斯說。但是,“聯邦政府花在四年制高等教育機構上的錢,遠比花在技能培訓項目上的錢多得多。”
關於如果 AI 掏空了大面積的工作該怎麼辦,主意多得是:全民基本收入(UBI)、不依賴僱主的福利、終身培訓、更短的工作周。每當技術焦慮達到頂點時,這些想法就會浮出水面;隨後又會同樣“理所應當”地消退,被成本、政治或一個簡單的事實擊敗——那就是它們需要一種美國幾十年來都未能實現的協作水平。
第 119 屆國會就像一艘幽靈船,被倦怠感和逃避艱難選擇的慾望操縱著。而 AI 行業正投入數千萬美元,確保沒人能奪走船舵。僅舉一例,一個名為“引領未來”(Leading the Future)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據報道已獲得硅谷風投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 提供的 5,000 萬美元承諾,以及 OpenAI 聯合創始人格雷格·布羅克曼夫婦提供的另外 5,000 萬美元。該機構計劃“積極反對”來自兩黨的、威脅行業優先事項的候選人。而這些優先事項總結起來就是:快速前進。不,再快點。
舒勒告訴我,AFL-CIO 將繼續向國家民選官員施壓,要求制定以工人為核心的 AI 議程,但“這場博弈在聯邦層面的激烈程度,可能不如在州層面”。超過 1,000 項 AI 相關法案正在各州議會醞釀。當然,AI 的資金也會跟到那裡;“引領未來”已經宣佈計劃將重點放在紐約州、加利福尼亞州、伊利諾伊州和俄亥俄州。
行政部門幾乎將所有的 AI 監管權都委託給了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名義上他是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的聯席主席,但在功能上,他更像是一個“政府角色扮演者”,同時維持著風險投資人和播客主持人的身份。薩克斯同時還是白宮的加密貨幣沙皇,他參與撰寫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國 AI 行動計劃》。
《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發現,薩克斯在至少 449 家與人工智能有關聯的公司中擁有投資。這已經不單是“狐狸看守雞舍”了,他還開直播!
AI 還是個新事物。它可能成長為以難以想象的好方式改變我們的生活。但它也提出了關於安全、不平等以及一個工資勞動體系可行性的深刻問題,這個體系儘管有缺陷,卻孕育了人類歷史上最繁榮的社會。而且毫無跡象——完全沒有——表明我們的政治體系有能力應對即將到來的變化。
這意味著人工智能提出的最深挑戰,可能根本不是針對就業。
最後的警告
“天哪,民主教科書裡的理想狀態,”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說,“是和平地表達和解決分歧,否則這些分歧可能會以更具破壞性或暴力的方式爆發。所以你會希望一個強大的民主國家能夠消化這類變化。”
克萊格曾任英國副首相和自由民主黨黨魁。他在脫歐後失去了議會席位,隨後移居加利福尼亞,在 Facebook/Meta 負責全球事務長達七年,在 2025 年返回倫敦之前,他成了某種擁有既定期權的“托克維爾”。克萊格告訴我,許多政府“根本沒有手段”來應對 AI。
他懷疑,最能平穩度過未來幾年的社會,是像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那樣的小型同質化社會,他們能夠進行成熟的對話——他們會組建“由某位睿智的前財政部長領導的委員會,拿出一份完美的藍圖,然後大家達成共識去執行。一百年後,他們依然會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社會”。或者是那些拒絕進行對話的大型集權社會。中國作為美國主要的 AI 競爭對手,一再展示了其在無需徵求同意或沒有拖延的情況下,推行快速且覆蓋全社會的變革的能力。
“如果民主政府只是隨波逐流地進入這一時期,而這一時期可能需要比他們目前表現出的能力更快速的變革,”克萊格警告說,“那麼民主將無法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
接著,他通過 Zoom 進行了一場極具英國特色的勵志演講,結合了丘吉爾式的堅定以及對美國那種延續了幾個世紀的“絕處逢生(走運)”的某種略帶優越感的調侃。“你們非常有活力,”他開頭說道,“有多少次人們曾預言美國不行了,這真的很了不起。”
如果政治被視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加里·彼得斯將無法參與其中,因為他明年就要退休了。馬喬裡·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是國會中在保護勞動力免受 AI 衝擊方面口才最好的共和黨倡導者(真的),她已經辭職了。吉娜·雷蒙多正被視為 2028 年潛在的總統競選者,她是一個有能力在“加速 AI 發展”與“謹慎管理”之間取得平衡的中間派。但這個問題不太可能等到那個時候。彼得斯說:“我們正進入一個似乎一天比一天更不穩定的世界。這種不確定性創造了焦慮,而焦慮有時會導致人們在行為和投票方式上發生劇烈轉變。”
這就說到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早在 AI 還處於理論階段時,他就一直在思考一個被 AI 塑造的未來。桑德斯用他那熟悉的斷奏語調告訴我:“AI 和機器人本質上是邪惡或恐怖的嗎?不。我們已經看到了它們在醫療保健、藥物製造、疾病診斷等方面的積極進展。但這裡有一個簡單的問題:誰將從這種轉型中受益?”
在 2025 年“對抗寡頭”巡迴演講的愛荷華州達文波特站,當他提到 AI 時,臺下觀眾發出了噓聲。桑德斯這位極度依賴“直覺”的政治家,能感受到數十年來積壓的憤怒——關於貿易、不平等、生活成本、系統性不公、政府對企業的效忠——正凝聚在 AI 這個焦點上。
10 月,他發佈了一份關於 AI 與就業的“95 條論綱”式報告。報告中引用了所有那些關於就業末日即將來臨的 CEO 和諮詢公司的危言聳聽,並提出了縮短工作周、加強勞動者保護、利潤分享,以及一項未指明的“針對大公司的機器人稅”,其收入將用於“造福受到 AI 傷害的工人”。這是一份充滿憤怒的文件,彷彿桑德斯是用拳頭敲出來的。
至少有一位民粹主義政治家認為桑德斯做得還不夠。
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在華盛頓特區的聯排別墅離最高法院非常近。他以其標誌性的造型迎接了我:迷彩工裝褲,一件黑襯衫,外面套一件棕襯衫,再套一件黑色紐扣襯衫。他已經好幾天沒刮鬍子了。如果他建議我們去吃潛艇三明治,或者組建民兵,我都不會感到驚訝。
班農確實有一些,怎麼說呢,流氓氣質。但他絕不是個 AI 門外漢。2000 年代初,他還是一名電影製片人時,就曾試圖購買雷·庫茲韋爾《奇點臨近》的版權,那是 AI 運動的聖經,預言了機器超越人類智慧的那一天。班農覺得那會是個好紀錄片。幾年前,他為自己的《作戰室》(War Room)播客聘請了一位 AI 記者,他追蹤每一份企業裁員公告,尋找預兆。
他擔心失控的 AI 會製造病毒和奪取武器——國家安全官員、生物安全研究人員和一些著名的 AI 科學家也同樣清醒地持有這種擔憂——但他認為美國勞動者正面臨如此迫切的危險,以至於他準備拋棄部分意識形態。“我主張拆解行政國家,但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班農告訴我,“你確實必須擁有一個監管機構。如果你不為這件事建立監管機構,那就乾脆把整套系統推倒算了,對吧?因為監管機構本來就是為了這種事而建的。”
班農想要的不僅是監管。他呼喚一個老觀念:即當政府認定一項技術具有戰略重要性時,政府應該擁有其中的一部分所有權——就像當年的鐵路,以及 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短暫入股銀行那樣。他指出了唐納德·特朗普在 8 月做出的“英明”決定,即讓聯邦政府持有英特爾 9.9% 的股份。但他認為,在 AI 領域的持股需要大得多——這應與流向 AI 公司的聯邦支持規模相匹配。
“我不知道——作為起點,持股 50% 吧,”班農說,“我意識到右翼會瘋掉的。”但他認為,政府需要向這些公司的董事會派遣具有良好判斷力的人。“而且你必須現在、現在、現在就切入這一點。”
相反,他警告說,我們正面臨著“系統中所有最糟糕元素的匯合——貪婪和慾望,加上那些只想抓取原始權力的人——全都在向這裡匯聚”。
我指出,監督這種匯合元素的人,正是班農曾協助當選的同一人,而且他最近還建議此人應該連任第三屆。
“特朗普總統是個偉大的商業天才,”班農說。但他從埃隆·馬斯克、大衛·薩克斯和其他人那裡獲得了“選擇性的信息”。班農認為這些人跳上特朗普的戰車只是為了最大化他們在 AI 領域的利潤和控制權。“如果你注意到,當我提到‘特朗普 2028 ’時,這些人並沒有歡欣鼓舞。我沒聽到一聲‘幹得好’。”他說,“他們利用了特朗普”,並預見到共和黨內部即將發生重大分裂。
班農的政治色彩自然不利於跨黨派聯盟的建立,但 AI 甚至打亂了他對界限的感知。他和格倫·貝克(Glenn Beck)簽署了一封聯名信,要求禁止開發超人工智能,擔心比人類更聰明的系統無法被可靠地約束;加入他們的還有傑出的學者和前奧巴馬政府官員——“那些寧願往地板上吐唾沫也不願承認自己和史蒂夫·班農在任何事情上站在一起的左派”。他一直在勾畫應對未來所需的聯盟理論:“這些倫理學家和道德哲學家——你必須把他們,說實話,和一些‘街頭鬥士’結合在一起。”
“馬蹄鐵”議題——極右翼和極左翼立場接觸的地方——在美國政治中非常罕見。它們往往出現在某些高度專業的問題(如 1896 年的金本位制,或 2008 年的次貸危機)鍊金般地轉化為某種情感波動(如威廉·詹寧斯·布萊恩的“黃金十字架”,或茶黨運動)時。這就是民粹主義。而民眾暴動的威脅偶爾使美國資本主義更加人性化:八小時工作制、週末和最低工資都從改革與革命之間的空間產生。
沒人比班農更瞭解或更能利用那個模糊地帶。他關於 AI 的憤怒可能在這一刻聽起來很理性,下一刻就變得極具威脅。當我們討論運行最強大 AI 實驗室的那些人時,他說:“我們就直白點吧”:“我們現在的處境是,坦率地說,一些在光譜上並非完全成年的人——從他們的行為就能看出來他們不是——正在為整個物種做決定。不是為這個國家,而是為這個物種。一旦我們觸及那個拐點,就再也沒有回頭路了。這就是為什麼必須阻止它,我們可能不得不採取極端措施。”
民眾暴動的麻煩在於,一旦你鼓勵所有人抓起它們,可能產生的破壞就永無止境。而且與早期時代不同,我們現在是一個被兩個物體定義的社會:一個是能讓每個人看清別人過得有多好的手機,另一個是如果他們決定做點什麼就會用上的槍支。
如果美國的精英們能在不被恐懼驅使的情況下負責任地行動,美國會更好。如果CEO們記得公民也是某種股東。如果經濟學家在未來進入後視鏡之前就嘗試建模。如果政治家選擇他們選民的就業而非他們自己的。這一切都不需要革命。它只需要每個人都把他們已有的工作做得更好。
對所有人來說,都有一個基本的起點——這個門檻極低,甚至可以被視為對這個共和國的一項基本認知測驗。
埃裡卡·麥肯塔弗(Erika McEntarfer)曾任勞工統計局局長,直到 8 月因為發佈了一份疲軟的就業報告而被特朗普解僱。麥肯塔弗在勞工統計局並未看到政治干預的證據,但她告訴我:“獨立性並非經濟數據面臨的唯一威脅。資金和人手不足同樣是危險。”
大多數試圖弄清 AI 對勞動力需求影響的經濟論文都在使用 BLS 的“當前人口調查”(CPS)。“這是目前最好的來源,”麥肯塔弗說,“但樣本量相當小。只有6萬戶家庭,20年來沒有增加。回應率一直在下降。”
要弄清我們的經濟發生了什麼,顯而易見的第一步就是擴大調查的樣本量,並增加一份關於工作中 AI 使用情況的補充調查。這隻需要額外增加幾個經濟學家和幾百萬美元——這是一筆微不足道的投資。但幾十年來,BLS 的預算一直在縮減。
美國成立 BLS 是因為其相信,民主政體的首要職責是瞭解其民眾的處境。如果我們弄丟了這種信念——如果我們不能逼自己去衡量現實;如果我們連“計數”都懶得去做——那麼,祝我們在面對這些AI機器時好運。
Twitter:https://twitter.com/BitpushNewsCN
比推 TG 交流群:https://t.me/BitPushCommunity
比推 TG 訂閱: https://t.me/bitpu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