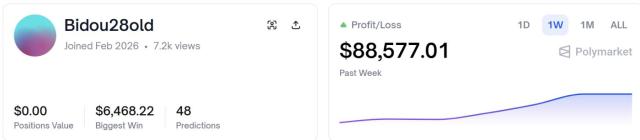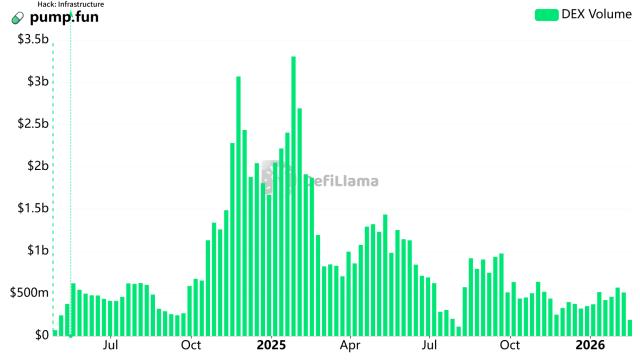Anthropic 在 12 日宣布完成 300 億美元的 G 輪融資,估值來到 3,800 億美元。新加坡主權基金 GIC 和 Coatue Management 聯合領投,其他投資方還包括 D.E. Shaw、Dragoneer、Peter Thiel 的 Founders Fund、阿布達比的 MGX 基金…微軟和 Nvidia 也參與其中,投入了此前承諾的 150 億美元中的「一部分」。
這是 2026 年至今最大的融資交易,也是有史以來第二大的風險資本融資,僅次於競爭對手 OpenAI 在 2025 年的 400 億美元。
而串投資人名單背後揭露一個現實,從紅杉資本到 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從高盛到摩根士丹利,從黑石到貝萊德,超過 30 家機構擠進了這一輪。其中紅杉同時持有 OpenAI、xAI 和 Anthropic 三家公司的股份。
在矽谷,投資同一賽道的直接競爭對手,曾經是一條不可觸碰的紅線,但在 AI 時代被碾碎了。
一條不成文的規矩
在矽谷的風險投資界,有一條存在了四十年的不成文規矩:不投競爭對手。
邏輯很簡單。當你投資了一家公司,你承諾的不只是資金,還有信任。你會坐進董事會,看到商業機密、產品路線圖、客戶資料、財務數據。如果你同時投資了它的直接對手,你怎麼證明自己沒有把 A 的情報帶給 B?
這不只是道德問題,更是商業信譽問題。在一個靠口碑運作的行業裡,「背叛創辦人信任」這個標籤,比一筆失敗的投資更致命。
這就是為什麼 Khosla Ventures 的創辦人 Vinod Khosla 在 2025 年公開表示,他「不會同時投資直接競爭的 AI 公司」。Thrive Capital 也選擇了忠誠:all-in OpenAI,拒絕其他 AI 大模型的誘惑。
但紅杉不這麼想。
2024 年底,紅杉經歷了一次世代交接。長期掌舵的 Roelof Botha 卸任全球管理合夥人,由 Pat Grady 和 Alfred Lin 接棒。新的領導團隊做出了一個激進的決定:同時押注 AI 的三匹頭馬。紅杉持有 OpenAI 的早期股份,後來投了馬斯克的 xAI,現在又出現在 Anthropic 的投資人名單上。
不只是紅杉。Altimeter Capital 向 Anthropic 投了超過 2 億美元,同時持有 OpenAI 的股份。Blackstone 向 Anthropic 投了約 10 億美元。阿布達比的 MGX 基金同時投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矽谷最聰明的錢,正在同時買進賽道裡的每一匹馬。
燒錢的速度
為什麼投資人願意打破禁忌?因為 AI 是一場沒有人輸得起的軍備競賽。而軍備競賽的第一條法則是:你不能停下來。
Anthropic 的年化收入(ARR)已攀升至 140 億美元,連續三年維持十倍以上的年增長率。年付費超過 100 萬美元的企業客戶,在兩年內從 12 家增至超過 500 家,該公司預計到 2026 年底,年化收入將突破 300 億美元。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增長引擎是 Claude Code:一個能幾乎不需要人類介入就能編寫和除錯程式碼的程式助手。這個產品的年化收入已達 25 億美元,今年初以來翻了一倍,企業客戶貢獻了超過一半。目前,GitHub 上 4% 的公開程式碼提交已是由 Claude Code 完成的。
Anthropic 財務長 Krishna Rao 在官方聲明中說:
無論是創業者、新創公司,還是全球最大的企業,客戶傳達的訊息都一樣:Claude 正日益成為企業運作方式中更關鍵的一環。這輪籌資反映了我們從客戶端看到的驚人需求,我們將利用這筆投資,繼續打造他們所信賴的企業級產品與模型。
近來,Anthropic 的技術也在震撼金融市場。本月初,該公司悄悄發布的一款可自動化處理特定法律工作的工具,引發了法律服務類股票的連鎖下跌。隨後又推出一款針對企業任務(包括金融研究)優化的新 AI 模型,導致金融服務公司股價走低。
但收入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支出。
Anthropic 在 2025 年僅在 AWS 的運算資源上就花了 26.6 億美元。加上研究人員薪酬、資料採購、GPU 集群建設,Anthropic 的年度總支出遠超收入。公司預計最早要到 2028 年才能實現損益平衡。
白話來說,這是一家年化收入 140 億美元、但依然在燒錢的公司。它需要不斷融資,不是因為它不成功,而是因為成功的代價比收入增長得更快。
這就是 AI 大模型商業的殘酷真相。你的收入可以像火箭一樣增長,但你的運算成本會比火箭更快,每一代前沿模型的訓練成本都是上一代的 3 到 5 倍。
Anthropic 已宣布將斥資 500 億美元在美國興建資料中心,德州和紐約的設施預計在今年內啟用。此外,該公司計劃使用 Google 價值數百億美元的專業 AI 晶片。然而,這些投資比起 OpenAI 仍是小巫見大巫,OpenAI 承諾在未來幾年內投入超過 1.4 兆美元於 AI 基礎設施,同時也在尋求籌集高達 1,000 億美元的新一輪資金。
這就解釋了 300 億美元融資的必要性。Anthropic 不是在籌集「成長資金」,它是在購買生存權。
害怕錯過的邏輯
那麼,回到核心問題:為什麼投資人願意同時下注多家 AI 公司,甚至不惜打破四十年的行業禁忌?
答案藏在一個更深層的恐懼裡。
2025 年,全球 AI 領域的總投資額超過 1,500 億美元。但這些資金高度集中,流向了不到五家公司:OpenAI、Anthropic、xAI、Google DeepMind、Meta AI。這場競賽的入場券,已經貴到只有主權基金和頂級 VC 才付得起。
在這種環境下,錯過贏家的代價,遠大於押錯一匹馬的損失。
假設你是紅杉。如果你只投了 OpenAI,而最終 Anthropic 贏了。你不只損失了 Anthropic 的回報,你還會被歷史記住為「那個錯過 AI 時代最大贏家的基金」。在風險投資行業,聲譽比單筆回報更值錢。一個錯過了 Google 的基金,和一個投了 Google 但也投了 Yahoo 的基金,後者的名字會被記得更久。
所以對沖不是策略,是保險。
但這裡有一個悖論。當所有聰明錢都在對沖同一個賭注時,它們實際上在做的,不是分散風險,而是把整個 AI 產業變成一個巨大的資金池。無論哪家公司最終勝出,資本都能確保自己站在贏家的一邊。
而那些無法參與這場對沖遊戲的人:小型 VC、個人投資者、普通員工,則被排除在外。他們只能選一邊,然後等待。
出走者的公司
為了理解 Anthropic 的今天,讓我們先回到 2020 年 12 月的一場離職。
達里歐 Dario Amodei 曾是 OpenAI 的研究副總裁。他在 OpenAI 的四年裡,主導了 GPT-2 和 GPT-3 的開發,兩個改變了整個 AI 產業軌跡的模型。在他加入時,OpenAI 還是一家非營利研究實驗室。在他離開時,它已經變成了一家微軟持股 49% 的商業公司。
2020 年底,達里歐和妹妹丹 Daniela Amodei 一起遞出了辭呈。據多位知情人士描述,分歧的核心是安全與商業化之間的路線之爭。達里歐認為,隨著模型能力飛速提升,OpenAI 在安全研究上的投入和決策權正被逐漸稀釋。微軟的百億美元投資,加速了這一趨勢。
翻譯過來就是,當你的最大金主說「快點做出產品」,安全研究員的話語權就會被壓縮到角落裡。
2021 年 1 月,達里歐帶著 7 名 OpenAI 的核心研究員創辦了 Anthropic。他們的使命很明確:建立一家「負責任的 AI 公司」,在商業成功和 AI 安全之間找到平衡。公司的名字來自希臘語「anthropos」,意為「人類」:一個帶有某種理想主義色彩的選擇。
五年後回頭看,這場出走的經濟規模令人震驚。2021 年 5 月,A 輪融資 1.24 億美元。2023 年,Google 領投,估值來到 41 億。2024 年,亞馬遜加碼,估值突破 180 億。2025 年 3 月,615 億。同年 9 月,1,830 億。
然後是 2026 年 2 月的 3,800 億美元。幾個月前才募得 130 億美元,最新一輪讓估值幾乎翻倍。Anthropic 同時宣布,將允許員工按這輪融資的估值出售持股。
Anthropic 用五年時間,從一間安全研究實驗室變成了全球最貴的 AI 公司之一,全球估值第四高的私人企業。融資總額接近 640 億美元。達里歐帶走的那 7 個人,如今支撐著一家員工超過 1,500 人的公司。
禁忌消失之後
但諷刺的是,支撐 Anthropic 背後一切的不是安全敘事,而是軍備競賽的邏輯。投資人押注 Anthropic,大多不是因為它更安全,而是因為他們不能承受不在場的後果。
在 AI 時代,忠誠是一種奢侈品。矽谷四十年來的不成文規矩:不投競爭對手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大多數市場有足夠的時間讓贏家和輸家自然分化。你可以花五年、十年觀察一個賽道,再決定把錢押在哪裡。
但 AI 不一樣。這場競賽的時間窗口太短,賭注太高,參與者太少。在這種條件下,對沖不是背叛,是理性。而當所有人都選擇理性時,禁忌就不再是禁忌了。它只是一條被所有人默契地跨過的線。
因為在矽谷,真正的禁忌從來不是投資競爭對手。而是錯過下一個時代。